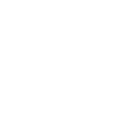全文
屋里很暗,只有桌上那枚玉简幽幽地发着光,映着父亲僵直的脊背。林晚躲在门框边的阴影里,手指抠着粗糙的木纹,抠得指甲缝里生疼。她十五岁了,不是完全不懂,坊市里流传的画本,同门师姐们偶尔压低声音的嬉笑,零零碎碎,拼凑出一些模糊的影子。但那些影子和玉简里流淌出来的画面,全然不是一回事。
光影晃动,里面那个女人……是母亲。穿着她从未见过的、几乎不能蔽体的纱衣,脸颊是不正常的潮红,眼神涣散,嘴角却挂着痴迷的笑。她在爬,向着光影另一端那个倚在榻上的身影,像……像一条狗。林晚的胃猛地抽搐起来。那身影,即使只是一个侧影,也带着压倒性的、令人不适的俊美与邪气,她知道那是谁,谢无妄。合欢宗的少宗主,不到二百岁的元婴修士,母亲奉命讨伐的目标。
母亲发出呜咽般的声音,夹杂着破碎的哀求,是林晚从未听过的娇媚,又浸满了某种屈辱的痛苦。她攀附上去,身体像蛇一样扭动,蹭着那人的腿。然后光影颤动,角度变换,一些更不堪的部位,更癫狂的起伏,更加……快乐的呻吟和哭泣混杂在一起的声音,一股脑地冲进林晚的眼睛和耳朵。她看见了母亲脸上那种表情,快乐到扭曲,痛苦到迷醉,仿佛沉在最深的泥淖里,却仰望着唯一的光。
恐惧像冰水,从头顶灌到脚底。她浑身发冷,牙齿磕碰出轻微的声响。恶心感翻涌上来,堵在喉咙口。她应该移开眼,应该冲进去砸了那玉简,应该……可她像被钉在了原地。除了恐惧和恶心,还有些别的。父亲宽阔的背影,对着这淫靡的光影,两天了,一动不动,一言不发。那股沉默像山,压得她喘不过气,那里面透出的不是愤怒,不是悲伤,而是一种……死寂的,令人心慌的麻木。她忽然恨起这沉默来,比恨光影里的谢无妄更甚。为什么不动?为什么不说话?为什么不……
光影终于结束了,很短,又好像长得没有尽头。屋子里只剩下玉简黯淡的微光。父亲终于动了一下,很慢,像生锈的傀儡。他抬手,似乎想碰那玉简,指尖在毫厘之处停住,然后蜷缩回来。他转过头,目光空洞地扫过门口阴影里的林晚,好像没看见她,又好像看见了,但那里面的东西已经熄灭了,映不出任何倒影。
“忘了吧。”他的声音嘶哑干裂,像砂纸磨过木头,“好好活着。”
说完,他站起身,空着手,拉开门。外面的天光漏进来一瞬,刺痛林晚的眼睛。他就那样走进了光里,背挺得很直,脚步很稳,一次也没有回头。门在他身后轻轻掩上,隔绝了光,也隔绝了他。
林晚慢慢从阴影里挪出来,走到桌边。玉简安静地躺在那里,冰凉。她伸出手,指尖触到那光滑的表面,猛地一缩,又坚定地握紧,抓起来,死死攥在掌心,硌得生疼。她不会忘。
***
大约一年后,一处阴湿的古修洞府。空气里是尘土和某种陈腐的味道。林晚抹去嘴角的血迹,谨慎地绕过地上几处早已失效的禁制残痕。洞府深处,两具相拥的白骨倒伏在地,衣物法宝早已风化,指骨却还紧紧扣在一起。她在白骨边不远处,一个腐朽的玉匣夹缝里,抽出了一本薄薄的册子。
册子封皮破损,前面几个字模糊难辨,只勉强认出“心经”二字。下面有一行后来加上去的、歪歪扭扭的小字:“稍有不慎,万劫不复。”
她靠着冰冷的石壁,翻开册子。不是功法,不讲灵力运行,不论天道感悟。它只讲一种“关系”,一种“认知”。修习者需认定一“主”,于内心彻底自视为其所有物,甘受一切驱策凌虐,并在此过程中,将施加于身的痛苦、耻辱、恐惧,悉数转化为无上快感,以此为引,反向缠绕、渗透、滋养“主”的意志,使其沉溺,最终无形无影,反客为主。
万劫不复?她低头看看自己沾满尘土和血迹的手,筑基后期的修为在这偌大修真界微若萤火。她还有什么可失去的?母亲还在合欢宗,父亲不知所踪。掌心似乎还残留着那枚玉简冰硬的触感,以及光影里母亲那张沉溺的脸。
她闭上眼,深吸一口洞府里污浊的空气。再睁开时,眼底那点属于十六岁少女的惊惶迷茫,被一种近乎冷酷的沉寂覆盖。她需要力量,一种能打破现状、能把谢无妄拖下来的力量。万劫心经,正是这唯一的稻草。
***
合欢宗山门外的桃花开得正好,靡靡的粉,甜腻的香,与远处云雾缭绕的仙家气象格格不入。林晚穿着最素净的衣裙,脸上没什么表情,对守门弟子说:“我要见谢无妄。”
通报的弟子回来得很快,眼神古怪地引她进去。穿过重重殿阁,空气里的甜香越来越浓,夹杂着若有若无的呻吟与调笑。她被带到一处开阔的露台,水榭风帘,谢无妄斜倚在软榻上,衣襟半敞,手里把玩着一只白玉酒杯。他抬眼看来,目光像带着钩子,划过她的脸,她的颈,她的胸脯,最后落回她眼睛里。
“哦?”他尾音上挑,饶有兴致,“林家的那个小丫头?胆子不小。”
林晚挺直脊背,压下喉咙的干涩,直视他:“放我母亲回玄天宗。我自愿留下,做你的炉鼎。”
谢无妄笑了,笑声低低的,震得空气里的甜香似乎都在颤动。“炉鼎?”他放下酒杯,站起身,走近她。元婴修士无形的威压随着他的步伐弥漫开来,并不暴烈,却黏稠得让人呼吸困难。他伸手,指尖拂过她的脸颊,冰凉。“就凭你,筑基后期?”他的气息喷在她耳廓,“还是说……你觉得你比你母亲,更有趣?”
屈辱感瞬间冲上头顶。林晚指甲掐进掌心,用刺痛保持清醒。她强迫自己不要躲闪,甚至微微抬了抬下巴,迎上他审视的目光:“你可以试试。”
谢无妄盯了她片刻,那双风流多情的桃花眼里,闪过一丝新奇的光,像看到什么好玩的玩具。“有意思。”他收回手,“好啊。你母亲,我会让人送回玄天宗。至于你……”他唇角勾起,“希望你别让我太快失望。”
母亲被送走的那天,林晚站在远处廊柱的阴影里看着。母亲眼神依旧有些空茫,但已能自己行走,身上穿着整齐的玄天宗服饰。她没有看向林晚的方向,或者说,她看任何方向都像隔着一层雾。林晚心里空了一块,又沉甸甸地塞满了别的东西。她转身,走向谢无妄指定的那座偏殿。
没有用药。谢无妄似乎想看看,她能“自愿”到什么地步。
一开始只是裸身。命令很简单:“爬过来。”光洁冰冷的玉石地面贴着皮肤,寒意直往骨头缝里钻。林晚垂下眼,一步步爬向榻上那个身影。她能感受到目光落在自己背脊、臀腿的每一寸,带着玩味的打量。她在心里默念《万劫心经》开篇的口诀,将那份几乎要将她淹没的羞耻感,想象成另一种东西的触角,顺着脊柱爬升。
舔脚。他的脚很干净,甚至有种玉石的质感,但终究是脚。她闭上眼,凑上去,舌尖触到的瞬间,胃部一阵痉挛。心法运转,痉挛被强行扭转为一阵细微的战栗,她告诉自己,这是臣服的快乐。
裸体侍奉他用餐、斟酒。他的手指偶尔会“无意”般擦过她的乳尖,或是腰侧。每一次触碰都让她肌肉绷紧,又在心法的作用下,将那紧张化为一股股酸麻的热流,悄悄汇聚到小腹。
他给她戴上了项圈,黑色的皮革,衬得她脖颈愈发白皙纤细。然后是乳环,冰凉的金属穿过敏感的尖端时,她疼得闷哼一声,眼泪不受控制地涌上来。他托着她的乳房打量,像欣赏一件物品的完成。“不错。”他说。疼痛尖锐,耻辱深重。林晚咬住下唇,疯狂运转心法,剧烈的痛苦像被投入熔炉的冰块,嘶嘶作响,蒸腾起令人头晕目眩的、扭曲的快意。她发现自己竟然……湿了。
后来是铃铛,系在项圈和乳环上,一动就叮铃作响。他让她扭动腰肢,摇着臀“跳舞”。铃声响得杂乱,她肢体僵硬,脸上烧得厉害。他看了直笑,不是愉悦的笑,是逗弄猫狗似的笑。她用指甲狠狠掐着大腿内侧,在心法的熔炉里,把这份难堪也烧成燃料。
再后来,绳子捆住了她的手腕、脚踝,将她以屈辱的姿势吊起来。耳光扇在脸上,火辣辣的疼,眼前发黑。鞭子抽在背脊、臀腿,留下纵横交错的灼痛。他有时会当着他那些下属、宾客的面这样对她,让他们点评,让他们取笑。那些目光像针,扎在她早已麻木又异常敏感的皮肤上。每一次公开的羞辱,都让心法的运转更加狂暴,痛苦与耻感被碾碎、重组,爆发出几乎令她崩溃的猛烈快感。她开始在高潮时失禁,喷溅的水液打湿地面,引来更多的嘲笑。而她在一片空白的眩目里,只记得死死咬住那心法的一线清明。
他终于占有了她。不是在榻上,是在露台边缘,背后是万丈悬崖和翻腾的云海。从后面,极其粗暴,没有任何温存,只有纯粹的发泄和征服。她疼得抽搐,喉咙里发出小兽般的哀鸣,又被顶撞得支离破碎。心法自发地疯狂运转,将撕裂般的痛楚与深重的践踏感,搅拌成泥泞而汹涌的狂潮,将她一次次抛上浪尖。最后他按着她的头深喉,窒息感与饱胀感逼出她的生理泪水,精液从嘴角和鼻孔流出,粘腻腥膻。她瘫软在地,剧烈咳嗽,浑身狼藉,眼神失焦,可身体深处却还在余震般轻轻抽动,泛着餍足的酸软。
他让她在人来人往的回廊角落自慰,用手指,用他随手扔给她的玉势。让她衣衫不整地去庭院里取东西,然后就在假山后、花丛边被他按住。她越来越分不清,那些在被凌虐时翻涌的、几乎淹没神智的快感,有多少是为了修炼心法,又有多少……是她这具身体,或者说她这个人,贪婪地渴求着的。
她偷偷藏起了那枚玉简。在夜深人静,谢无妄不在时,她会拿出来,注入微弱的灵力。光影重现,母亲的脸,母亲的声音。仇恨应该像火一样烧起来。可看着看着,她的手会不由自主地滑下去,滑到双腿之间。影像里母亲沉沦的模样,谢无妄施加在她身上的种种,混淆在一起。快感涌上来,凶猛而熟悉。她在高潮的颤抖里,死死盯着光影中母亲欢愉痛苦交织的脸,心头猛地窜过一个冰冷的念头:凭什么,她能那么早就……这个念头让她悚然一惊,随即被更多的快感和随之而来的空虚吞没。
谢无妄确实变了。在她面前,他不再总是那副高深莫测、慵懒风流的模样。他的欲望和脾气都更加直接。命令简短粗暴:“跪好。”“爬过来。”“自己动。”调教的手段愈发狠戾,花样百出,似乎笃定她无论承受什么,都能从中榨取出快乐,并反馈给他更炽烈的反应。他会在她濒临崩溃的高潮后,随手丢给她一瓶合欢宗的正统丹药,或者一部不错的双修功法。有一次,他拎着一条几乎透明的纱裙和带着细链的脚环扔给她,随口道:“试试这个。”
最让她心惊的,是那次激烈的纠缠后,他汗湿的胸膛贴着她汗湿的背,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绕着她项圈上的铃铛。寂静中,他忽然低笑一声,气息喷在她耳后:“林晚,”他很少叫她的名字,“你给我下了什么蛊?”
她的心脏几乎停跳。心法已成本能,无声无息地运转着。她僵硬着,不敢回答。
他也没要答案,只是又笑了一下,那笑声里听不出喜怒,然后手臂收紧,将她更深地勒进怀里。
《万劫心经》的运转越来越流畅,像呼吸一样自然,不再需要她刻意维持。她甚至感觉不到它在运行,只是痛苦越来越少,快感越来越清晰、轻易,仿佛那本就是她应得的奖赏。
然后,在那个毫无征兆的夜晚,一次格外漫长和暴烈的调教之后,她被吊在梁上,浑身遍布鞭痕与吻痕,铃铛随着身体的颤抖细碎地响。谢无妄用一根镶着软玉的细棒,极其缓慢地碾磨着她最敏感的那处。快感堆积得如山如海,将她抛起又摔落,意识浮沉。就在某个临界点,仿佛体内有什么东西“咔嚓”一声轻响,碎了,又重组了。
海潮般的高潮席卷而过,留下战栗的躯体。但这一次,有些不一样。她清晰地感觉到,一道无形的、坚韧的丝线,从她灵魂最深处蔓延出去,另一端,轻轻搭在了谢无妄的心神之上。一种明悟升起:她可以顺着这条线,传递一个念头,一个命令,而他,不会察觉异常,只会觉得那是他自己的意愿。
恐惧,毫无来由的巨大恐惧,瞬间攫住了她,比第一次看到母亲影像时更甚。她几乎要尖叫出来。不,不是这样。她不要这样控制他。她想要……想要他真正地想要她,想要他更狠地对待她,想要他眼中只有她,而不是因为一条无形的线。
她没有传递任何念头。她只是在高潮的余韵里,细微地发着抖,像秋风里的落叶。
自那以后,谢无妄身边再没有出现过别的女人。他每日将她带在身边,无论是处理宗门事务,还是外出赴宴。调教依旧,甚至更频繁,但他也开始跟她说话,说一些无关的事,天气,某处新发现的秘境,某场无聊的拍卖会。他让她留宿在他的主殿,有时只是搂着她,什么也不做。有一次,他抚摸着她的头发,忽然问:“林晚,你恨我吗?”
她蜷在他怀里,沉默了很久,久到他以为她不会回答。她轻轻摇了摇头,脸埋得更深。恨吗?那最初的火焰,似乎早已被无数次的潮汐扑熄,只剩下灰烬里一点灼烫的、辨不清成分的残渣。
再后来,他筹备了一场道侣大典。声势不大,却极尽合欢宗之奢靡。他说,要光明正大地娶她。
大典那日,林晚穿着繁复华丽的红色礼服,层层叠叠的纱裙,勾勒出窈窕身姿。妆容精致,眉眼如画,额间一点花钿,衬得她肤白如雪,气质清冷,竟真有几分玄天宗那些仙子们的出尘味道。宾客不多,但都是合欢宗有头有脸的人物,目光或好奇,或玩味,或了然,投注在她身上。
她看着铜镜里的自己,有一瞬间的恍惚。这身打扮,这个身份……道侣?一股莫名的慌张攥住了她的心。她忽然想起了很久以前,那个昏暗的屋子,父亲对着玉简一动不动的背影,还有他最终走入光里,再也没有回头的决绝。
典礼的流程一步步进行。交拜,敬酒,接受祝福。谢无妄一直牵着她的手,唇角带笑,应付自如。他的手掌温暖干燥,握得有些紧。林晚的心却越来越空,越来越慌,像踩在云端,不知何时会跌落。
临近尾声,宾客微醺,气氛松弛。谢无妄忽然侧过头,凑近她耳边,温热的气息拂过她的耳垂,声音带着笑意,只有她能听清:“准备好了吗?”
林晚一愣,还没明白他话里的意思,也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。
下一刻,他松开了她的手,动作快得只余一道残影。不知何时,一柄温润的玉尺出现在他掌心。在周围宾客尚未收敛的笑容里,在摇曳的烛火和飘散的香雾中,那玉尺带着细微的破空声,极其响亮地、重重地抽打在她被华丽礼裙包裹的臀上。
“啪——!”
清脆的声音在骤然寂静下来的大殿里回荡。
不是疼。
是炸开。
一股无法形容的、从骨髓深处爆发出来的酥麻酸软,伴随着灭顶的快感,如同被点燃的火药桶,瞬间席卷了她每一根神经,每一个细胞。礼服下,铃铛疯狂地震响。她双腿一软,连惊叫都来不及发出,就彻底瘫倒在地上。
身体完全失控。痉挛从脚趾尖窜上头顶,又狠狠砸回小腹深处。她仰起头,脖颈拉出脆弱的弧线,喉咙里溢出破碎的、不成调的呜咽。礼裙的下摆迅速晕开深色的水渍,并且范围不断扩大,一股又一股温热的水流,完全不受控制地从她腿间喷涌而出,溅湿了光洁的地面,发出细微的滋滋声。她蜷缩起来,又无力地伸展开,指尖徒劳地抠抓着地面,全身都在剧烈地颤抖,高潮的余波一浪高过一浪,持续不断,仿佛永远不会停歇。眼前光影乱颤,意识模糊,可偏偏昏不过去,清晰地感受着每一寸肌肤的颤栗和羞耻。
好久,久到像过了一辈子。颤抖才稍微平复了一点,只剩下细微的、无法抑制的抽搐。她浑身湿透,头发黏在潮红的脸颊上,眼泪鼻涕糊了一脸,狼狈不堪地瘫在水渍里。
谢无妄就站在她面前,居高临下地看着。他脸上依旧带着笑,那笑却与方才不同,充满了毫不掩饰的欲望,和一种近乎宠溺的、看着自己最得意作品的神情。他转向呆若木鸡的宾客们,优雅地欠了欠身,语气轻松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:“内子有些特殊的……喜好。让诸位见笑了,扰了雅兴,改日再赔罪。”
说完,他弯下腰,一把将瘫软如泥的林晚打横抱了起来。华丽的裙摆逶迤在地,拖出一道湿痕。他没有走向后殿,而是就站在大殿中央,手臂用力,轻易地分开了她还在轻轻痉挛的双腿。
冰凉的空气瞬间贴上最隐秘湿热的肌肤。
“不……不要……”林晚发出细微的、带着泣音的哀求,徒劳地挣扎了一下,手无力地推拒着他的胸膛。
但他的手臂像铁箍。她的身体,她最私密不堪的部位,就这样毫无遮挡地、完全地暴露在数十道目光之下。那些目光,惊愕的,了然的,兴奋的,鄙夷的……像烧红的针,扎在她每一寸皮肤上。
更可怕的是,这一次,他甚至没有碰她。
仅仅是被这样看着,被这极端耻辱的认知包裹,那股刚刚平复些许的、灭顶的快感,就如同被投入滚油的冷水,轰然再次爆开!比上一次更猛烈,更疯狂!
“啊——!!!”
她终于尖叫出来,声音嘶哑破碎,身体向后反弓成惊人的弧度,脖颈上的项圈铃铛疯狂作响。又一股更汹涌的水流喷溅而出,这次溅得更远,甚至有几滴落在了近处宾客的衣摆上。高潮来得毫无道理,连绵不绝,一次紧跟着一次,强度不断攀升。她感觉自己像暴风雨中的小船,被狂浪反复抛掷、撕碎。意识在极致的快感和极致的羞耻中反复灼烧,想要昏迷逃避,可心法大成后那过分清醒的感知,却让她连这一点解脱都得不到。她只能清晰地感受着每一次痉挛的抽搐,感受着温热的液体如何不断涌出,感受着那些目光的凌迟。
唯一能做的,就是勉强抬起颤抖得不成样子的手,死死捂住了自己的脸。仿佛这样,就能遮住一点羞耻,虽然徒劳。
指尖冰凉,脸颊滚烫。泪水从指缝里不断渗出。
谢无妄抱着她,看着她在他怀里崩溃、失禁、高潮不断,看着她捂着脸无声哭泣颤抖。他脸上的笑意更深,眼底翻涌着黑暗的满足和某种近乎温存的东西。他低下头,吻了吻她汗湿的鬓角,用只有她能听到的声音,温柔地说:“乖,我的母狗仙子。你今天很好看。”
林晚在持续不断的高潮痉挛中,听到了这句话。那冰冷的恐惧,那无措的慌张,忽然间都沉淀了下去。取而代之的,是一种尘埃落定的、近乎解脱的认命,以及在这认命之下,悄然涌出的、让她自己都战栗的安心与归属。
她放下了捂着脸的手,露出那张被泪水、汗水和欲望浸透的、狼狈却异常艳丽的容颜。眼神涣散了一瞬,然后,慢慢地,聚焦在谢无妄含笑的脸上。
她张了张嘴,声音沙哑得不像话,却异常清晰地,一字一句地,在寂静的大殿里响起:
“是……主人。母狗林晚……求您……继续。”
大殿里,只剩下她细碎的呜咽,铃铛的轻响,和某些压抑不住的、兴奋的抽气声。
***
修真界很大,也很小。合欢宗少宗主娶了个来历特别的道侣,道侣在大典上当众出了点“小状况”,这消息在某些圈子里悄悄流传,又被某些人默契地按下。玄天宗那边,似乎收到了什么交换,保持了沉默。林晚这个名字,渐渐成了合欢宗内一个讳莫如深又引人遐想的符号。
后来,林晚陆陆续续听说,母亲回到玄天宗后,经过秘法治疗,忘记了合欢宗里大部分不堪的记忆,身体也逐渐摆脱了药物影响,重新开始修炼,只是性子比以往更沉寂了些。父亲呢,似乎彻底心灰意冷,远远离开了这片是非之地,在一个偏僻的散修聚集地,娶了一个修为不高但性情温和的女修,有了新的生活,新的家庭,将前尘往事彻底埋葬。
挺好的。林晚想。真的挺好。她拿出那枚保存了很久的玉简,指尖摩挲了一下,然后轻轻一握。玉简化作一撮细细的粉末,从她指缝间洒落,被风吹散,再无痕迹。
中州大陆西南,一座以繁华著称的修真城池“流光城”。市集熙攘,宝光氤氲,各色修士穿梭其间。
一对道侣格外引人注目。男子紫袍玉冠,俊美无俦,眉宇间风流自成,修为深不可测。女子依偎在他身侧,身段玲珑,容貌昳丽,一袭水红裙裳,外罩轻纱,眉眼低垂间有种惊心动魄的艳色,偏偏气质里又透着一丝难以接近的疏冷。两人携手而行,宛如画中走出的神仙眷侣,引来不少艳羡或探究的目光。正是林晚与谢无妄。
他们像最寻常的道侣一样,搭乘慢悠悠的公共云舟俯瞰城景,在热闹的集市摊位前流连,购买一些精巧但无关修炼的小玩意儿。谢无妄甚至会拿起一支玉簪,在她发间比划,问她好不好看。林晚脸颊微红,轻轻点头。
一切都那么正常,那么美好。
直到他们走到一处修士聚集较多的广场,正在观看中央喷泉随灵力变化而幻化的光影表演。
谢无妄忽然抬手,极其自然地,将她一缕被微风拂到颊边的发丝别到耳后。指尖不经意擦过她敏感的耳廓。“晚晚。”他微微俯身,低声唤她,气息靠近,带着淡淡的笑意,吹在她敏感的耳垂上。
就这一下。
“嗯……!”
林晚的身体猛地僵住。
《万劫心经》早已大成,与她的身心融为一体,对他任何形式的“触碰”和“指令”都敏感到了极致。这看似亲昵的举动,在无人知晓的契约里,不啻于最直接的调弄。
那股熟悉的、根本无法抗拒的酥麻电流,从耳垂瞬间窜遍全身,直冲小腹深处。双腿骤然发软,膝盖不受控制地内扣,剧烈地颤抖起来,几乎要支撑不住身体的重量。 小腹处肌肉疯狂痉挛,一股热流失控地涌出,瞬间浸透了最里层的薄衫,甚至隐约洇湿了外层的水红裙裳。
她死死咬住下唇,将一声冲到喉咙口的尖叫硬生生咽了回去,只发出一声极轻微的、带着泣音的呜咽。全身的力气都用来对抗那汹涌而至、几乎将她淹没的快感潮汐,克制着身体的颤抖。脸颊飞起红晕,眼眶迅速湿润,蓄满了生理性的泪水。她软软地倒进谢无妄及时伸出的臂弯里,脸颊埋在他胸前,浑身不受控制地细细颤抖,像秋风里最后一片叶子,小手无力地抓紧他胸前的衣料,指节泛白。
周围有人投来目光,好奇地打量着这对过分出众的道侣,见女子依偎在男子怀中,脸颊绯红,眼含水光,模样娇怯可怜,倒更添几分动人。只当是小女儿情态,或是有些不适,并无人深想。
谢无妄稳稳地揽着她,手掌在她背后轻轻拍抚,如同安慰。只有林晚能感觉到,他胸膛传来的低沉震动,那是他在笑。
“忍得住吗?”他传音入密,语气里带着毫不掩饰的兴味。
林晚说不出话,只能在他怀里极小幅度地摇头,又点头,眼泪蹭湿了他的衣襟。下面又是一股温热水流涌出,腿根一片湿滑黏腻。快感与羞耻在每一根神经上跳舞,将她反复抛起又摔落。
他低笑一声,揽紧了她,继续若无其事地往前走,仿佛只是体贴道侣稍作休息。
“乖,”他的声音直接响在她脑海,带着恶魔般的诱哄,“下一处,我们去看城西新开的那家灵兽苑,听说……很有趣。”
林晚闭上眼,长长睫毛上挂着泪珠,在渐浓的暮色和璀璨的灵力灯火映照下,微微颤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