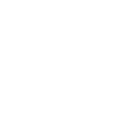4.生死搏斗
第十七日。
清晨落了一层薄雾。
我醒来时,雾正从帐幕边缘漫进来,灰白的、湿冷的,像无数细小的蛛丝缠上我裸露的脚踝。阿云嘎蹲在帐口,背对着我,正用一块粗布擦拭一柄短刀。
刀身不长,约莫成年人小臂,刃口有几处细小的卷边。他把布条缠在掌心,一下一下,从刀根推到刀尖,推得很慢。
他听见我起身,没有回头。
“那是我阿爸的刀。”他说。
我把羊皮裹紧,没有说话。
“他去年冬天死在铁门那边。”他把刀翻了个面,继续推,“尸体没找回来。秃鹫和狼分干净了。”他顿了顿。
“刀是后来从俘虏那里缴回来的。那人用我阿爸的刀砍过三个白狼部的牧人,血槽里还有没擦净的锈。”他把布条从掌心解下,刀柄朝前,递给我。
“你用它。”我接过刀。
刀刃比我预想中更轻,平衡点在刀根前三指。我把刀竖在眼前,刃口在雾光里泛着暗哑的灰,像冬眠未醒的蛇。
“谢了。”他站起身,拍膝上的土。
“不用还。”——雾没有散。
我穿过营地边缘那排废弃旧帐,脚掌踏过湿滑的碎石,每一步都陷进冰凉的泥里。炊帐方向没有升起炊烟——今日无人进食。祭台前的空地上,已经聚起了比昨日更多的人影,在雾里凝成一团团沉默的黑色块。
他们看见我。
人群自动裂开一道缝。
比昨日更宽,更沉默,更接近葬礼。
我穿过那道缝,脚掌踩进空地中央那片被千百双脚踩踏过的硬泥。雾太浓,浓到我看不清祭台边缘的兽骨旌幡,看不清那顶镶白狼尾的兽皮帐,只能看见空地尽头那团更浓的、正在缓缓移动的黑影。
他来了。
阿勒坦。
他的脚步很沉,每一步都像巨石滚过冻土。雾在他膝弯处缠绕、退散、又重新聚拢,露出他布满旧疤的小腿,露出膝甲边缘那圈磨亮的铜钉,露出他垂在身侧的那柄刀。
那刀比我的长三倍。
刃宽如掌,背厚如指,刀尖在雾里泛着冷白色的寒。
他走到空地中央。
离我十五步。
他站定。
雾从他的肩头滑落,露出那枚覆在额顶的白狼头颅。狼吻正对着我的眉心,两枚空洞的眼窝盛满灰白的水光。
他看着我。
那目光没有轻蔑,没有愤怒。
只有一种极深的、近乎疲惫的平静。
他开口。
“神女说过了。”他的声音很低,像从深谷里滚来的巨石碾过沙砾。
“你曾经是她最重要的男人。”他顿了一下。
“但是现在不是了。”我的手指在刀柄上收紧。
雾在沉默里缓缓流动。
“她恋旧情。”他说,“昨夜她求我——留你一条命。”他望着我。
“你现在放弃,还来得及。”他的语调没有起伏,像在陈述一桩已经反复思量过、终于做出决断的交易。
“神女确实不能给你。但作为补偿——”他侧过头,朝人群边缘说了句什么。
雾太浓,我看不清那个方向。只看见一团更纤瘦的黑影从人群里被推出来,踉跄两步,停在空地边缘。
是个少女。
她披着一整块未鞣制的青灰色狼皮,从肩头裹到膝弯。雾里看不清脸,只看见狼皮边缘露出的一截细白手腕,和腕骨上一圈骨珠链——比她脚踝那圈更细、更密,像雏鸟初生的绒羽。
阿勒坦没有看她。
他望着我。
“这是我妹妹。阿吉奈。”他顿了顿。
“你可以娶她。”人群里涌起一阵低低的嗡鸣。那嗡鸣里有惊诧、有艳羡、有隐隐的不解——白狼部头人的胞妹,草原上多少武士求娶不得的明珠,被这样轻描淡写地许给一个连羊群都没有的南边牧人。
阿吉奈没有动。
她站在空地边缘,狼皮边缘露出一截细白的脚踝,脚趾紧紧抠进泥里。
阿勒坦继续说。
“除此之外,给你五十头牛,三百只羊。两顶新帐,一顶冬用厚毡,一顶夏用薄纱。三匹战马,鞍具自选。”他停了一下。
“你可以留在白狼部,也可以带着你的女人、牛羊、帐马回南边。草原不拦离去的客。”他的目光落在我脸上。
“只一个条件。”“永远不再踏进神女十步之内。”雾很静。
静到我听得见自己胸腔里那颗心脏缓缓收缩、扩张、再收缩的声音。
阿吉奈还站在原地。她的脚趾在泥里越抠越深,整条细白的小腿都在轻微颤抖。
我没有看她。
我看着阿勒坦。
“谢谢你的慷慨。”我的声音比预想中更稳。
“但是——”我把阿云嘎那柄短刀从腰侧拔出,横在身前。刀身在雾里亮了一瞬,又沉进灰白的水光。
“我是她的男人。”阿勒坦的眼睛微微眯起。
“你会为她死。”“你会为她不惜一切。”我说,“我也是。”他沉默。
很久。
然后他点了点头。
那动作很轻,轻到几乎看不出弧度。可他肩头那枚白狼头颅的獠牙在雾里晃了一下,像从一场漫长的梦里醒来的第一道战栗。
“我明白了。”他抬起手。
人群边缘涌出两名武士,抬着一具沉重的木架。架上陈列着兵器——不是陈列,是堆砌。长矛、短斧、青铜钺、镶银骨朵、带倒刺的飞索。刃口在雾里泛着冷光,像一窖尚未启封的冬雪。
“你挑。”他说。
我走向木架。
没有看那些长矛。没有看那些短斧。没有看那柄柄身镶满绿松石的青铜钺,也没有看那根曾在无数场决斗中敲碎头骨的镶银骨朵。
我的手越过它们。
从木架最边缘、最不起眼的角落里,拾起一柄小刀。
那刀很短,比我掌心长不了多少。刃口有锈,刀柄裹着的皮绳早已磨秃,露出底下暗黄的骨片。它太轻了,轻到握在手里几乎没有重量。
我把短刀插进腰侧。
另一只手探进羊皮内袋。
金属的凉意贴上指尖。
我把那东西抽出来。
雾很浓,浓到人群边缘那些模糊的面孔看不清我掌中这具小小的轮廓。可阿勒坦看得见。
他低下头。
他盯着我手里那具黑色的、塑料质感的、与他所见过的任何兵器都不相似的造物。
他皱起眉。
那困惑又回来了。不是愤怒,不是轻蔑——是那种幼狼初见不曾见过的猎物时,瞳孔深处缓缓漾开的、介于好奇与犹疑之间的波纹。
“你用什么?”他问。
“这个。”我把气枪平举在胸前。
“还有这柄刀。”他沉默。
他的目光从我掌心那具黑色的造物缓缓移到我脸上,又从我的脸缓缓移回我的掌心。他的眉心越皱越紧,那道竖纹深得像刀劈斧凿。
“你要用这些……玩具,”他的声音很慢,每一个字都在舌底反复碾磨,“和我决斗?”“是的。”我把气枪握稳。
“就是用这些玩具。”他望着我。
很久。
雾在我们之间缓缓流动,把他庞大的身形切割成无数道浓淡不一的灰影。我看不清他的表情,只看见那枚白狼头颅两枚空洞的眼窝,正对着我的眉心。
他没有笑。
他没有任何轻蔑的表情。
他只是望着我,像望着一件他无法理解的、不属于这片草原也不属于任何战场的异物。
然后他点了点头。
“来。”他把那柄长刀横在身前。
刃宽如掌,背厚如指,刀尖直直指向我喉咙下方三寸。
“让我看看你的玩具。”我握紧枪柄。
十二枚钢珠在内胆里轻轻滚动,像十二粒冰凉的雨滴。
雾还在下。
空地边缘,我听见母亲终于没有忍住的那一声极轻的、破碎的抽气。
我没有回头。
十五步。
我用枪口抵住阿勒坦的眉心。
***母亲冲出来的时候,雾正散到最薄。
不是从人群边缘悄悄挤入。是撞开了那些沉默围观的武士,撞开了两名持矛守卫横挡的臂,撞开了一切试图阻拦她的手臂与目光——她赤着脚,踩过晨露未干的硬泥,踩过昨夜雨水积成的大小水洼,踩过这片即将染血的土地。
她扑在阿勒坦身前。
那身祭服在奔跑中彻底散了。
原本斜勒左乳的窄幅兽皮滑落了半截,整片左乳完全袒露在薄雾里——浑圆,饱满,乳尖因剧烈运动与清晨寒气挺立成深褐色的一粒,随着她急促的喘息上下弹跳。那枚朱砂痣在乳缘微微颤动,像一颗即将从熟透果实表面滑落的樱桃。
腰侧那根系带早不知何时崩开了。整片小腹毫无遮拦地暴露在晨光里——平坦,柔软,脐窝深深的,腹肌在剧烈呼吸下一道道绷紧又松开。腰窝那两枚小小的涡正对着阿勒坦垂落的手掌,仿佛还在等待那枚拇指重新按上来。
臀。
她的臀部在奔跑时颠出了惊心动魄的波浪。
那片短得过分的后幅皮料早已歪到腰侧,整个浑圆硕大的臀峰完全裸露在空气里——两轮雪白的满月,因奔跑与恐惧而绷出最饱满的弧线。臀肉在每一步落地时剧烈震颤,像盛满琼浆的羊皮囊即将被最后一滴撑破。那震颤从臀峰一路传导到大腿后侧,在那片丰腴的、泛着细密红痕的皮肉上荡开一层层乳白色的涟漪。
大腿根部的骨珠链早已歪了,细密的骨粒深深勒进腿肉最嫩的深处,勒出一道浅浅的、泛着湿润粉色的凹痕。她跑得太急,那圈链子几乎要嵌进皮肉里,可她浑然不觉。
她扑倒在阿勒坦膝边。
双手撑在他沾满晨露的胫甲上,扬起脸。
那张脸上全是泪。
不是昨夜那种无声的、大颗滚落的泪珠。是决堤的、失控的、从眼眶深处不断涌出又不断被新泪覆盖的滔滔水流。睫毛膏彻底化开了,在她颧骨上晕成两片青灰的湿痕。嘴唇在剧烈颤抖,下唇那道刚愈合的血口重新裂开,沁出一粒猩红的血珠。
“不要……”她的声音碎成千万片,“不要杀他……”她望着阿勒坦。
不是望我。
是望他。
“他是我的儿子……”她终于说出来了。
这句话像从肺叶最深处被生生剜出,带着血、带着肉、带着她来到这个世界十七夜里所有不敢言说的恐惧。她的整个身体都在剧烈颤抖,那对裸露的乳在颤抖中反复碰撞、弹开、再碰撞,乳尖磨蹭出细密的湿痕。
“他只是个孩子……他才十六岁……”她攥住阿勒坦垂落的手掌,把那枚宽大的、布满旧疤的手掌按在自己颤抖的胸脯上,按在那枚朱砂痣旁。她的手太冷了,冷到贴着他掌心的皮肤瞬间泛起一层细密的鸡皮疙瘩。
“求你……”阿勒坦低下头。
他望着她。
那眼神里没有愤怒,没有被冒犯的羞恼。只有那团越来越浓的、他不知如何命名的困惑,和困惑深处某种正在缓慢碎裂的东西。
他没有回答她。
可他的手在她掌下没有抽离。
然后她抬起头。
她终于看见了我。
看见了我手中那柄平举的、黑色塑料质感的、十五步外正正指向阿勒坦眉心的造物。
她的瞳孔骤然收缩。
那收缩太剧烈了,剧烈到她整张脸的血色都在同一秒褪尽。颧骨上那两片青灰的泪痕在这一刻突然变得刺目,像刚刚凝结的伤口。
她放开阿勒坦的手。
她转向我。
膝盖在泥地里碾过,骨珠链深深嵌进腿肉,她浑然不觉。
她望着我手里的气枪。
“不……”那声音不再是哀求,是近乎窒息的气音。
“你不能……”她的眼睛从枪口缓缓移向我。
那眼神我从未见过。
不是六岁高烧时她三天三夜未合眼的凝视。不是十二岁她把被欺负的我搂进怀里时的沉默。不是十六岁她坐在“蓝月”后巷水泥台阶上哭了整整一小时、抬起脸来的那一眼。
那里面有恐惧。
不是为阿勒坦。
是为我。
“放下……”她的声音在颤抖,每一个字都在舌尖碎裂。
“求你……放下……”她跪在泥地里,赤裸着胸脯与腰腹与雪白浑圆的臀,膝头深深陷进冰凉的湿泥,那圈骨珠链在她大腿根部勒出更深的红痕。她的双手朝我伸着,指尖在晨雾里微微痉挛,像溺水之人伸向最后一根浮木。
“阿勒坦是好人……”她的眼泪还在流,可她已经顾不上擦。
“他救了我……那些士兵要把我拖去慰劳全军……是他把我从他们手里要过来……”她的声音越来越低,低到几乎被雾吞没。
“他没有强迫过我……那夜他背我进帐,把我放在地铺上,自己睡在帐口……”她望着我。
“他睡在帐口,背对着我,整夜没有回头……”雾在她眼眶边缘凝成细碎的水光。
“他每天清晨去猎场,猎到第一只猎物,总是把最嫩的里脊留给炊帐,让老阿妈炖汤给我……”“他问过我疼不疼……那天祭台上的石棱割破我的脚,他看见了,蹲下来用袖子给我擦血……他的袖子是狼皮,很粗,擦得我脚背发红……可他不知道,他以为越用力擦得越干净……”她的声音哽咽了。
“他从来没有……从来没有在没有问过我之前……”她没有说完。
雾在这一刻骤然浓了。
阿勒坦动了。
他不知道母亲在说什么——那些绵长的、破碎的、不属于这片草原的音节。可他看见她跪在泥地里颤抖的背影,看见她朝我伸出的双手,看见她裸露的脊背上每一节因哽咽而突起的椎骨。
他站起来。
他绕过她,朝我走来。
“你的玩具。”他的声音很平静。
“让我看看。”十五步。
十步。
八步。
他的脚步很沉,每一步都像巨石滚过冻土。
他的眼睛望着我手里的枪,瞳孔深处那团困惑的雾正在缓缓散去。他没有恐惧,没有轻蔑,只有一种终于面对未知事物的、近乎虔诚的平静。
五步。
我扣动扳机。
砰——那声音在雾里炸开,不像枪,更像一截脆骨被生生折断。压缩空气从气室喷涌而出的尖啸,钢珠脱离磁轨的轻颤,以及——没入皮肉的闷响。
阿勒坦的头颅向后猛地一仰。
那枚白狼头颅的额顶绽开一朵猩红的花。血从狼吻与人类眉骨交界处涌出来,不是喷溅,是缓慢的、黏稠的、仿佛犹豫不决的渗出。那朵花在银白的狼毛上迅速扩大,像雪原上骤然盛放的罂粟。
他愣住了。
他没有倒下。他甚至没有踉跄。他只是抬起手,用指尖触碰自己眉心下方那枚正在汩汩流血的孔洞。
他把指尖送到眼前。
血是红的。
在他布满旧疤的掌心,那滴血像一粒尚未凝固的朱砂。
“妖法……”他的声音很低,像从很深很深的井底传来,“你用妖法……”他没有恐惧。
那语气里有困惑,有惊讶,甚至有一丝几乎听不出的释然。
——原来是这样。
——原来这就是她的世界里战斗的方式。
——原来我并非败给一个瘦弱的少年。
——我是败给她的神。
他朝我迈出一步。
我扣动第二次扳机。
砰——这一枪打在他的右眼。
钢珠穿透眼睑,没入虹膜,把那枚琥珀色的瞳仁击成一片浑浊的红白。他猛地偏过头,像被重拳击中侧脸,整个庞大的身躯朝左剧烈倾斜。血从眼眶边缘涌出,顺着鼻梁、颧骨、下颌,滴进他胸口那枚白狼獠牙吊坠的缝隙里。
他没有停。
他朝我迈出第二步。
砰——左眼。
这一次他看见了。他看见那粒细小的、银色的、快得根本无法捕捉的光朝他左眼飞来。他试图偏头,可那光太快了,快到他只来得及阖上半扇眼睑——钢珠擦过睫毛,没入眼球,把那枚同样琥珀色的瞳仁也击成一片模糊的猩红。
他发出一声低沉的、从胸腔深处挤出的闷哼。
不是哀嚎。
是痛极之后终于被允许发出的第一声呼吸。
他站在原地。
两只眼睛都在流血。血不是流,是涌,是从他眼眶深处不断挤出的、黏稠温热的暗红色泉水。他睁不开眼了——他的眼睑还在徒劳地翕动,睫毛被血黏成一簇簇倒伏的黑草。
他什么都看不见了。
可他还在朝我的方向。
他迈出第三步。
砰——第四枪打在他的颈侧。
不是喉结,是左侧颈动脉与锁骨交汇处那枚柔软的凹陷。钢珠撕裂皮肤,切断血管,在肌肉深处炸开一个小小的空腔。血不再是涌,是喷——一道细长的、猩红的弧线从他颈侧斜斜射出,在雾里划出半道残虹。
他的脚步终于乱了。
不是倒下。是他失去了方向。他试图朝前,身体却往右偏;他试图稳住重心,左膝却软了一瞬。那柄宽如掌、厚如指的长刀还握在他手里,可刀尖已经垂向地面,在泥里拖出一道歪扭的深沟。
他四处砍伐。
不是朝我。
是朝雾。
朝他再也看不见的、只剩下声音与气息的世界。刀锋破开空气,发出沉闷的呜咽。一刀,两刀,三刀——每一刀都落空,每一刀都砍在他以为我在的方向,可每一刀都与我擦过至少三尺。
他太急了。
血从他眼眶与颈侧同时奔涌,他撑不了太久。
我绕到他身后。
他的背脊很宽,肩胛骨在兽皮下隆起两座沉默的山丘。那枚白狼头颅的獠牙从他后颈垂下来,随着他沉重的喘息轻轻晃动。他还在朝雾里挥刀,刀刃卷了,血槽里嵌满他自己的血。
他忽然不动了。
他垂下刀。
刀尖插进泥土,支撑住他即将倾倒的身躯。
他没有回头——他回不了头,他的眼睛已经无法望向任何方向。他只是垂下那颗戴着白狼头颅的、仍在汩汩流血的额头。
“你……”他的声音很低,很慢,每一个字都像从血里捞出来。
“对她好一些。”我举起阿云嘎那柄短刀。
刃口朝下,刀尖对准他后颈第三与第四节椎骨之间的凹陷。
“阿勒坦。”他听见了。
他没有动。
“你是个好人。”他笑了。
那笑容在他满是血污的脸上绽开,像冬夜最后一片雪花落进将熄的篝火。他的嘴角扯动,牵动颈侧那道仍在喷血的伤口,血涌得更急了。可他还是在笑。
“我知道。”他说。
我用力刺下去。
刀刃切开皮肤,切断肌肉,在椎骨缝隙里发出一声细微的、清脆的——咔。
他的头颅向前垂落。
血从断口涌出,不是喷,是倾泻。像一只被不慎打翻的陶罐,盛满的深红色琼浆终于找到了倾注的出口。他的身体还在原地跪了几秒——膝头触地,双手垂落,那柄长刀从他掌间滑脱,倒在泥里,溅起一小片细碎的水花。
然后他向前扑倒。
白狼头颅从他额顶脱落,滚进血泊,两枚空洞的眼窝朝天仰着。
我拾起那颗头颅。
发辫很沉。他的头发很黑,编成一根粗长的独辫,辫尾系着一枚褪色的银环。我把银环解下来,塞进羊皮内袋。
然后我提着那颗头颅,转身。
母亲跪在十五步外的泥地里。
她望着我。
不,她望着我手里那颗还在滴血的头颅。
她的嘴唇张着。可发不出任何声音。她的喉咙里只有一种极轻的、像风穿过破损羊皮风箱的嘶嘶气音。她的眼睛睁得很大,大到虹膜边缘那圈灰蓝几乎要被瞳孔吞没。睫毛上还挂着泪,泪珠将落未落,在晨光里凝成两粒透明的冰晶。
她赤裸的胸脯剧烈起伏着。
左乳边缘那枚朱砂痣在惨白的皮肤上红得像另一道正在流血的伤口。腰侧那道系带早已不知去向,整片小腹与腰窝毫无遮拦地暴露在渐散的晨雾里。她的臀部还压在脚跟上,那两轮雪白的满月被挤压出更饱满的弧线,臀肉从大腿两侧溢出来,在泥地里碾出细密的红痕。
她望着那颗头颅。
望着阿勒坦阖不上的眼睑、血污覆盖的面容、嘴角那抹还没有完全散去的笑意。
她的嘴唇动了一下。
没有声音。
又动了一下。
还是没声音。
第三下。
一声极轻的、像幼兽濒死前最后半次呼吸的呜咽从她喉咙深处挤出来。
那不是哭泣。
那是灵魂从躯壳里被生生剥离时,韧带与筋膜断裂的余响。
她的眼睛阖上了。
不是慢慢阖上。是骤然断电般的、整扇眼睑同时坠落。她的身体朝一侧倾斜,赤裸的肩头撞进泥地,那对饱满的乳房在撞击下剧烈弹跳,像两只终于挣脱樊笼的白鸽。
她没有再睁开眼睛。
她躺在血泊边缘,躺在阿勒坦那柄长刀拖出的歪扭沟痕旁,躺在晨雾将散未散的第十七日清晨。
她赤裸的身体在青白的天光下白得像雪。
那圈骨珠链还深深勒在她大腿根部,勒出一道泛着湿润粉色的凹痕。
阿云嘎从人群边缘跑过来。
他的脸是白的,白到那颗缺了半边的门牙像第三只眼,正正嵌在他张开的嘴唇中央。他望着我手里那颗还在滴血的头颅,望着倒在血泊里的阿勒坦的无头躯体,望着我母亲赤裸昏迷的身体。
他什么也没说。
他只是弯下腰,扛起阿勒坦的头颅。
“你说过,”他的声音很轻,“如果看见阿勒坦忽然跪下去——”“现在呢?”我把短刀插回腰侧。
“现在去白狼帐后面等我。”他点头。
他扛着那颗头颅跑进雾里,跑向营地深处那顶镶白狼尾的兽皮帐。
我跪下去。
我把母亲从泥地里抱起来。
她很沉。她的身体太丰腴、太饱满了,每一寸皮肉都像灌满蜜与奶的羊皮囊,在我臂弯里软软地陷下去。她的头靠在我肩窝,散乱的长发垂落,发梢扫过我的手背。
她的呼吸很轻,很浅,像一根随时会断的丝线。
她没有醒。
我把她抱进怀里,站起来。
人群没有动。
那数百名围观的武士、妇人、孩子,还站在原地,像一尊尊被晨露打湿的石像。他们望着我,望着我怀里的神女,望着我腰间那柄还在滴血的短刀,望着我羊皮内袋里那具黑色的、塑料质感的、打穿他们王者头颅的造物。
没有人出声。
没有人阻拦。
我抱着母亲,穿过那道比来时更宽、更沉默、更接近葬礼的人肉窄巷。
雾散尽了。
第十八日清晨的阳光从云缝里刺下来,把整片营地照成一片苍冷的白。
雾没有散。
阿勒坦倒下去的时候,像一棵被雷从内部劈开的古树。他的膝盖先触地,然后是腰,然后是那具太过宽阔的、从未在任何人面前低伏过的肩背。白狼头颅从他额顶滑落,滚进泥里,两枚空洞的眼窝正正对着我脚边那柄锈迹斑斑的短刀。
他睁着眼睛。
眉心那一点红只有米粒大小,边缘洇开一圈极细的、几乎看不见的血线。钢珠卡在额骨与颅腔之间,不足半寸深,却足够切断一个王者所有的未来。
他的嘴唇翕动着。
不是诅咒,不是遗言。
是一个字。
一个我听得懂、却不愿意听清的字。
“……她……”他的眼睛越过我,越过雾,越过这片刚刚夺走他呼吸的空地,望向人群尽头那顶白狼尾帐。
帐帘垂着。
她的身影不在那里。
他的瞳孔散开了。
像一滴墨落入静水,缓缓晕染成雾。
我站在原地。
那柄气枪还举在胸前,枪口正对他眉心那道细小的血孔。我的手指僵在扳机上,过了很久,才一节一节松开。
塑料滑套还温热着。
十二枚钢珠还剩十一枚。
阿云嘎从人群边缘冲过来。他的脚步很急,溅起的泥点落在我赤裸的脚背上,冰凉。他蹲在阿勒坦身侧,伸出手,在那具还在轻微抽搐的颈侧探了一下。
然后他抬起脸。
他望着我。
那双十四岁的眼睛里没有恐惧,没有崇敬,甚至没有劫后余生的侥幸。
只有一种极深的、近乎荒诞的茫然。
“你杀了他。”他说。
我把气枪塞回羊皮内袋。
“嗯。”“你怎么……”他没有问完。
因为他看见了。
看见阿勒坦眉心那粒细小的血孔,看见那柄滚落泥地的白狼头颅,看见我掌心那具黑色的、从未在这片草原上出现过的造物。
他沉默。
人群也沉默。
那沉默不是等待,是溺水——千百个人同时被按进深水,张口无声,只能睁着眼睛望向漩涡中心那个瘦削的少年。
我转身。
雾还在下,把祭台前那片空地染成一片湿漉漉的灰。旌幡垂落,兽骨静默,连远处战马都噤了声。
而她——她跪坐在高台上那顶狼皮座边缘。
她的嘴唇张着,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那双眼睛死死盯着我——不是盯着我的脸,是盯着我手里那柄已经滑进内袋的气枪,盯着阿勒坦倒在雾里的、还在缓缓渗血的眉心,盯着我脚边那柄阿云嘎阿爸的短刀。
她的胸口剧烈起伏。
那片几乎完全袒露的左乳在急促的呼吸里上下弹跳,朱砂痣像一枚被惊飞的蝶,在她乳缘反复起落。兽皮祭服那根系带松了,整片布料斜斜挂在她肋侧,露出小半个平滑紧实的小腹。脐窝深深陷着,随她屏住的呼吸一收一缩,像一枚惊惶的眼。
她的脚踝还在流血——昨日祭台上那道细长的划痕崩开了,红线顺着脚背流进趾缝,滴在狼皮座边缘那枚白狼獠牙上。
她没有低头去看。
她只是望着我。
那眼神里有太多东西,多得我认不全。
恐惧。惊骇。难以置信。
还有一种极深的、从骨缝里渗出来的——骄傲?
“妈。”我的嘴唇动了动,声音很轻,轻到只有自己能听见。
她听见了。
她的睫毛剧烈一颤,两行眼泪无声滚落。
可她还是没有动。
她不敢动。
她是神女。是阿勒坦用一场决斗的赌注押在台上的战利品。而决斗还没有结束——不。
决斗结束了。
赢家是我。
我向她走去。
脚步很慢。每一步都陷进雾里湿润的泥土,每一步都踩过阿勒坦倒下去时溅开的血迹。那血迹还是鲜红的,在他银灰色的狼皮甲上洇开一大片,像一朵正在缓慢绽放的罂粟。
她望着我走近。
她的呼吸越来越急,胸口的起伏越来越大。那根系带终于彻底滑落,整片兽皮从她肩头垂下来,挂在肘弯,像一面投降的白旗。
她赤裸着上半身坐在那里。
左乳边缘那颗朱砂痣,乳尖在冷空气里悄然挺立。锁骨尽头那粒褐色的小痣,腰窝深处那两道深深的涡。所有这一切都在雾光里泛着细密的、汗湿的亮。
她没有躲。
她只是望着我。
我走到她面前。
停下。
我伸出手。
不是去触碰她赤裸的胸脯,不是去握住她垂落腰侧的手指。我的手悬在半空,距离她泪痕未干的脸颊只有三寸。
就那样悬着。
像十六年前那个六月凌晨,产房里那只迟迟不敢落下、怕惊醒这具刚从母体娩出的婴孩的第一只手掌。
她握住我的手腕。
她把我的手掌拉下来,轻轻按在自己濡湿的脸颊上。
她的皮肤是凉的。雾太冷,她在高台上坐了太久。
可她贴在我掌心的那块皮肤渐渐暖起来,暖起来,暖到微微发烫。
“你来了。”她说。
声音很轻,轻到几乎被风吹散。
“嗯。”“你真的来了。”“嗯。”她闭上眼睛。
泪珠从睫毛缝隙挤出来,滚过我的虎口,滴进掌心那道月牙形的浅疤。
很久。
我松开手。
我转身。
我走向高台边缘,走向那片千百人沉默围观的空地,走向阿勒坦倒下去时滚落泥地的白狼头颅。
我弯下腰。
拾起它。
那头颅很重。整块白狼头皮鞣制而成,狼吻还是张开的,露出四枚森白的獠牙。我把它举过头顶,让那两枚空洞的眼窝朝向天空,朝向这片被雾封住的、无风无日的穹顶。
我开口。
声音比我想象中更稳。
“神女——”我顿了一下。
“——现在是我的女人。”雾在沉默里缓缓流动。
“有谁赞同?”没有人说话。
“谁反对?”还是没有人说话。
人群像一片被冻结的海。千百个喉咙同时失声,千百双眼睛同时低垂,千百具躯体同时凝固成不会动的石像。
然后——第一个膝盖触地。
是阿云嘎。
他跪在阿勒坦的尸身边,膝盖陷进湿泥,额头低垂到几乎触地。那缺了半颗门牙的嘴紧紧抿着,像要把所有疑问、所有惊骇、所有对这个荒诞清晨的不解都抿碎在齿间。
第二个。
第三个。
第四个。
像多米诺骨牌依次倾覆,像熟透的麦浪被风成片压倒。跪地的闷响从空地中央层层扩散,传到人群边缘,传到炊帐方向,传到那顶镶白狼尾的兽皮帐前。
帐帘掀开一道缝。
老阿妈站在那里。
她没有跪。
她只是望着我,望着我手里那枚白狼头颅,望着高台上赤裸着上半身、泪痕未干的母亲。
很久。
她垂下眼睛。
她弯下腰,膝盖触地,灰白的辫子垂落在帐口石阶上。
“……白狼部的头人。”她的声音很低,像从干涸河床里挤出的最后一滴水。
她顿了顿。
“贺新主。”人群终于开口。
不是欢呼,是齐刷刷的低语,千百个喉咙同时念诵同一句我听不懂的古老祝词。那声音很低沉,很低沉,像潮水从远方一寸一寸逼近,像雷暴在天边缓慢滚动。
“……贺新主……”“……贺新主……”“……贺新主……”我没有动。
我站在高台边缘,左手举着那枚白狼头颅,右手垂在身侧。掌心那道月牙形的浅疤还在发烫,烫得像刚刚烙上去的印记。
身后传来极轻的窸窣声。
是兽皮摩擦兽皮的细响。
是她站起身时骨珠链轻轻碰撞的声音。
是她赤脚踏过狼皮座边缘、一步一步向我走来的脚步声。
我转身。
她站在我面前。
那件祭服已经完全滑落了。整片兽皮堆在她脚边,像一朵盛放至凋零的墨色大丽花。她赤裸着站在雾里,胸脯、小腹、大腿、脚踝上那圈骨珠链——所有这一切都在灰白的水光里泛着细密的、潮湿的亮。
她望着我。
然后她扑上来。
不是拥抱。
是扑。
她整个人撞进我怀里,双臂箍紧我的后颈,胸脯死死压在我胸口。那颗朱砂痣隔着两层薄薄的衣料——我的旧校服,她的赤裸皮肤——烙在我心脏跳动的位置。
她的嘴唇贴上我的脸颊。
不是吻。
是雨点。是骤雨。是十六年积压的恐惧、屈辱、绝望、以及此刻骤然决堤的狂喜同时化作的一场暴雨。她的唇从我颧骨碾到眼角,从眼角碾到眉心,从眉心碾到鼻梁,最后——最后落在我的嘴唇上。
她的舌尖抵开我的齿关。
我怔住了。
我的手指还握着那枚白狼头颅,僵在半空。我的嘴唇被动地张开,被动地接纳那条柔软湿润的、带着她体温和泪水的舌。
她的舌尖缠上我的舌尖。
不是蜻蜓点水。是交媾——唇舌的交媾,深入、缠绵、不留余地。她的舌面刮过我的上颚,刮过我的齿龈,刮过我能被她触碰到的一切。她的呼吸很急,急促到我几乎以为她会在下一秒窒息。
可她不肯停。
她的嘴唇死死压着我,像溺水的人衔住最后一口气。
然后她的唇移到我耳边。
“快——”她的声音极轻,轻到几乎是气声。可每一个字都像烧红的烙铁,烙进我的耳廓。
“伸出舌头。”我没有明白。
可我照做了。
我把舌尖探出唇缝。
她立刻含住它。
她的嘴唇包裹着我那片湿滑的软肉,像蚌含住一粒沙。她的舌面再次缠上来,这次更慢、更缠绵、更像某种公开的仪式。她的齿尖轻轻啮咬我的舌尖,一下,两下,不疼,却让我的脊椎像过电一样蹿过一阵麻痹。
她的唇再次贴上我耳廓。
“现在——”她的声音在颤抖。
“摸我。”我的手指没有动。
“快。”她的气息喷在我耳垂,潮湿、滚烫,“别忘记了——现在我是你的女人。”她顿了顿。
“按部族传统,胜利者要在第一时间享用战利品。”我的瞳孔骤然收缩。
我终于明白了。
她在表演。
这不是亲热。这是仪式。是草原上千年不变的、用身体确认归属的古老规则。我杀了阿勒坦,她是我的战利品。如果我不“享用”,人群就会困惑,就会猜测,就会质疑这场决斗的意义。
她必须被我占有。
在千百双眼睛的注视下。
“我……不懂……”我的喉咙发紧,声音几乎是从齿缝挤出来的。
她的唇又贴上来。
这次是真正的吻——嘴唇贴着嘴唇,像在安抚受惊的马驹。
“别怕。”她极轻地说,“跟着我做。”她的手握住我的手腕。
她把我的手拉到她胸前。
那里是赤裸的、温热的、随着她急促呼吸剧烈起伏的乳。她的皮肤比我想象中更滑,像最细腻的绸缎,又像刚刚凝住的乳酪。
她把我的手掌按在她左乳上。
正正按在那颗朱砂痣的位置。
“摸我胸。”她的声音很轻,轻到几乎听不见,“用力一点。让底下人看见。”我照做了。
我的手指收拢,陷进那团柔软饱满的、沉甸甸的肉。那触感太陌生了——不是舞台上隔着亮片短衫瞥见的遥远轮廓,是活生生的、会在我掌心轻微颤动的、被我的体温渐渐捂热的皮肤。
她的乳肉从我的指缝溢出来,泛着细密的淡红。那颗朱砂痣嵌在我虎口边缘,像一枚被我们共享的印记。
人群爆发出一阵低沉的嗡鸣。
不是惊骇。是满足。是饥饿已久的狼群终于看见猎物被撕开的确认。
她的唇又贴上我耳廓。
“摸我屁股。”我的手从她胸前滑落,沿着腰侧那道深深的弧线,覆上她赤裸的臀。
那臀太丰满了。我的手指完全陷进去,像陷进两团刚刚揉好的面团,温软、绵韧、带着微微弹手的张力。她的臀肉在我掌下轻轻颤抖,每一次颤抖都让那道深沟收得更紧。
我捏了一下。
很轻。
她的呼吸骤然急促。
“用力。”她的气息喷在我颈侧,“让他们看见。”我用力。
五道指痕立刻浮现在她雪白的臀肉上,像刚刚烙上去的红印。
人群的嗡鸣变成欢呼。
“再摸大腿。”她的声音几乎带上了哭腔——不是痛苦,是某种更复杂的、我无法命名的情绪,“快。”我的手滑向她大腿。
那腿太长了。从我腰侧一路延伸下去,每一寸弧度都饱满得像要化开。我的手指覆上她大腿内侧那寸极少示人的软肉,那里比胸脯更滑、更嫩、更敏感。我的指尖刚刚触到,她整个人都轻轻弹了一下。
我用整个手掌抚上去。
从膝弯一路向上,推进到大腿根部,推进到那丛掩映在骨珠链边缘的深色软毛边缘。她的皮肤在我掌下一寸寸泛起粉红,像熟透的蜜桃被阳光一寸寸染上颜色。
她没有躲。
她只是把脸埋在我颈窝,双臂死死箍着我的后颈。她的整个身体都在轻微颤抖,从肩胛到腰窝,从臀峰到腿根,每一寸皮肉都在我掌下细微地痉挛。
可她没有让我停。
因为这是仪式。
因为胜利者必须在众人面前“享用”他的战利品。
因为只有这样,他们才会相信。
欢呼声终于彻底爆发。
不是祭天求雨时那种虔诚的低语,是粗野的、放纵的、带着酒意与原始欲望的嘶吼。男人把拳头擂向胸口,女人把孩子举过头顶,连那些持矛的武士都用矛尾杵击地面,发出一片沉闷如雷的鼓点。
他们在祝福。
祝福这场刚刚完成的归属仪式。
祝福白狼部有了新的头人。
祝福神女终于有了真正的“主人”。
我的手掌还停在她大腿内侧。
她终于抬起头。
她的眼眶还是红的,睫毛上挂着没干的泪珠。可她的嘴唇弯着,弯成那种我太熟悉的、面对客人时的标准微笑。
只有我看见她眼底那层薄薄的、即将碎裂的冰。
“现在,”她的声音很轻,只有我能听见,“牵我进帐。”我握住她的手。
她的手很凉。骨节在我掌心一根根凸起,像冬天落尽叶子的细枝。
我牵着她走下高台。
人群自动让开一条路。
比来时更宽,比来时更静。千百双眼睛追随着我们交握的手,追随着她赤裸背上那几道浅红的指痕,追随着我腰侧那柄还沾着阿勒坦血迹的短刀。
我们走过阿勒坦的尸身边。
他的眼睛还没有阖上。
那瞳孔散得很开,像一片被搅浑的深潭。他的嘴唇还是张着的,那个没有说完的字卡在齿间。
“……她……”我停下脚步。
母亲也停下。
她低头望着他。
雾还落在他脸上,把那些凝固的表情都晕成模糊的水彩。他的眉心那粒细小的血孔已经不再渗血,边缘凝成一圈黑褐色的痂。
她看了他很久。
然后她松开我的手。
她弯下腰。
她的手指极轻地覆上他的眼睑。
从上往下,慢慢抹过。
他的眼睛阖上了。
她站起身。
没有回头。
我们走向那顶镶白狼尾的兽皮帐。
帐帘垂着。老阿妈跪在帘边,灰白的辫子垂落石阶,额头低低触着冰凉的青石。
她没有抬头。
我掀开帐帘。
光线从身后涌进来,把帐内那张铺满兽皮的地铺照出一角银灰的绒光。空气里有她昨夜残留的体温,有晚香玉香水即将散尽的气息,有阿勒坦裹伤用的草药辛辣。
她走进去。
我跟进去。
帐帘在我身后垂落。
隔断所有目光。
她背对着我。
帐内很暗。只有顶窗一道细缝漏下天光,正正照在她赤裸的肩头。那片皮肤上还有昨夜阿勒坦指腹摩挲过的淡红,还有今晨她自己咬出的齿痕,还有方才我留下的、正在渐渐转成青紫的五指印记。
她没有动。
很久。
然后她转过身。
她的脸上没有泪。
可她的眼眶是红的,红得像那粒被她含在舌尖反复碾磨的、我从未听清的音节。
她望着我。
“你真的来了。”这是她第三次说这句话。
可这次不是陈述。
是疑问。
我点头。
“嗯。”她沉默。
帐外传来欢呼声。有人在唱我听不懂的祝酒歌,有人在用矛尾击地,一遍一遍,像巨人的心跳。
她望着我。
然后她伸出手。
不是拥抱,不是亲吻。
她的手贴上我的脸颊。
拇指轻轻摩挲我眼角那道熬夜留下的青黑,摩挲我因连日饥饿凹陷下去的颧骨,摩挲我下颌那几根刚刚冒头的、还未来得及剃去的胡茬。
“你长大了。”她说。
我的喉咙发紧。
“嗯。”她的拇指停在我嘴唇上方。
“那个人——”她顿了顿,“他今天本来想留你一命。”我知道她说的是谁。
“我知道。”“他昨晚问我,”她的声音很轻,“你是不是我的儿子。”我沉默。
“我说不是。”她还是说了。
不是否认我是她的儿子——而是承认我是她的男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