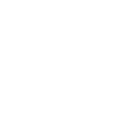3.为了夺回妈妈,我发出决斗邀请
3.为了夺回妈妈,我发出决斗邀请
2026年2月13日首发于禁忌书屋
必须要夺回母亲,这念头像一根刺。
起初只是扎在指腹,细得看不见,走路时不觉得,握拳时也不觉得。可每当我在营地某个角落远远望见那顶镶白狼尾的兽皮帐——望见帐帘掀开一道缝,望见老阿妈端着陶罐进去又出来,望见黄昏时分阿勒坦的身影从帐口映出,被篝火拉成一道沉默的长影——那根刺就往里深一寸。
一寸。
又一寸。
今夜它抵到了骨头。
我蜷在那顶废弃帐幕的夹缝里,膝盖顶着胸口,后背抵着冰凉的兽皮。白日偷来的半块干肉压在舌底,被我反复咀嚼成毫无味道的纤维渣,仍舍不得咽。
远处传来笑声。
是营地里那群赤脚少年围坐在篝火边,用我听懂了大半的西南口音争抢一块烤焦的肩胛骨。缺门牙的那个赢了,把骨头高高举过头顶,像举着一面旗帜。
他们笑得很响。
我没有笑。
我在想阿勒坦。
那个只比我大一两岁、却高过我两个头的年轻王者。那个把母亲的黑丝袜缠在腕间、系成一个歪扭蝴蝶结的少年。那个蹲下身、用自己舌尖濡湿的拇指去按母亲唇上血口的男人。
他背她进帐的时候,手指陷进她大腿后侧那团最软的肉里。
他把她放在那张铺满兽皮的地铺上时,是不是也像放一件易碎的瓷器?
他凝视她赤裸的身体时,瞳孔深处那片困惑的饥渴,今夜是否已经变成了别的什么?
——变成熟稔。
——变成习惯。
——变成那种清晨醒来时自然而然伸向枕边的手臂。
我把舌底那团干肉纤维咽下去,噎得喉结生疼。
——
第二夜。
我在炊帐帮那个缺门牙的少年劈柴。他叫阿云嘎,今年十四岁,父亲死在去年冬天与铁门那边的一场边界冲突里。他说这话时正在把木柴码成一摞,语气平淡得像在说羊圈里又死了两只羔。
“铁门是什么?”我问。
他抬头看了我一眼。篝火映在他脸上,把那颗缺了半边的门牙照成一个黑洞。
“你不知道铁门?”
“我是南边来的。”我说,“很远很远的南边。”
他接受了这个解释。草原上的人对“很远”有天然的敬畏,不问缘由。
“铁门是天边的一道裂缝。”他把一根歪扭的木柴掰正,膝盖压住一端,用力下折——咔嚓,“有人说那是天神发怒时劈开的伤口,有人说是上古大战留下的遗迹。反正每隔一阵,门那边就会掉东西出来。”
他顿了顿。
“或者掉人。”
我握住斧柄的手指收紧。
“掉……什么样的人?”
“什么都有。”阿云嘎把那根掰断的木柴扔进柴堆,“去年掉下来一匹铁铸的马,比真马还大,肚子里全是会转的轮子。萨满说那是邪物,熔了铸矛头。”
“前年掉下来一个人。男的,穿得很怪,说的话谁也听不懂。头人把他赏给了白狼帐的老阿妈当奴隶,没活过三个月。这里太冷了。”他搓了搓手臂,像在验证自己还活着。
我没有再问。
我把斧刃狠狠劈进下一根木柴。
——
第四夜。
我摸清了营地所有的哨位。
白狼帐外围固定有四名守卫,子时换岗,交接时有大约二十次呼吸的空档。帐后有一处兽皮缝补处,老阿妈每天丑时三刻会掀帘出来,去炊帐取第二日清晨的热水。她走得很慢,每一步都像在数脚下的石子,从帐口到炊帐大约需要三百次心跳。
三百次心跳。
足够我进去。
足够我把帐内那张铺满兽皮的地铺看个清楚。
足够我看见——
看见什么?
我把那念头再次按进喉咙。
还没有到时候。
——
第七夜。
阿云嘎啃着那块永远啃不完的肩胛骨,忽然问我:“你每天望白狼帐,是在望什么?”
我的手指在柴堆边缘停了一瞬。
“没有望。”
他咧嘴笑,黑洞正对着我。
“你望的是神女吧。”
我沉默。
“大家都这么传。”他把骨头换到左手,右手在裤腿上蹭了蹭油,“说新来的牧羊人每天傍晚都站在旧帐那边,一动不动望白狼帐的帘子。有人猜你是铁门派来的细作,有人猜你是被神女迷住了——她跳舞那天你也在,对吧?我看见你了。”
他还是笑着,缺了半边的门牙像一道缩小的、不曾流血的伤口。
我没有否认。
“她是我母亲。”
这句话说出口之前,我并不知道自己要说。
它自己从喉咙里挤出来,像一根卡了七天的刺,终于被体温与唾液磨穿了表层,噗地露出尖。
阿云嘎的骨头停在半空。
他看着我。篝火在他脸上跳跃,把那道黑洞照得更深。
“……亲生的?”
“亲生的。”
他沉默了很久。
久到我以为他会站起来走掉,或者像营地那些成年人一样,露出那种“原来如此”又“那又如何”的复杂表情——既怜悯,又疏离,还有一丝隐隐的、对神女世俗身份的敬畏褪色后残余的困惑。
可他只是把那块肩胛骨放回膝盖上。
“那你打算怎么办?”
他的声音很轻,不像十四岁。
“这里是草原。”他说,“白狼部的规矩,女人不是财产,抢来了就是自己的。哪怕是你亲娘,只要阿勒坦收下了她、让她住进白狼帐、给她穿上神女的祭服——她就是他的。”
他抬起眼睛。
“除非……”
“除非什么?”
他没有立刻回答。
篝火噼啪爆开一朵火星,落在他手背,他像没感觉到一样。
“除非有人挑战他。”
他的声音压得很低,低到几乎被风吹散。
“白狼部的男人,不分贵贱,都有权向占有了自己女人的男人提出决斗。赢了,女人归你。输了——”
他没说下去。
“输了怎样?”
“你会死。”他说,“阿勒坦十岁起就没输过。”
——
我躺在那顶废弃帐幕里,睁眼望着头顶一片漆黑的兽皮。
决斗。
这个词在我胸腔里反复碾磨,像一颗被含了太久的青梅,皮肉早已磨尽,只剩一枚又酸又硬的核。
我见过阿勒坦的身形。
肩宽是我两倍,臂围几乎抵得上我的大腿。他赤手空拳走过营地时,那些持矛的武士会不自觉地后退半步——不是敬畏王座,是对绝对力量的肌肉记忆。
而我。
高中柔道社,红黑带。全市青少年锦标赛六十二公斤级亚军。教练说我的关节技很漂亮,可惜爆发力不足,遇到力量型选手容易被反制。
这里不是垫满榻榻米的道馆。
这里没有裁判,没有限时,没有“有效”和“一本”之间那些精细的计分规则。
这里只有矛尖、刀锋,和两具肉体在尘土里翻滚到一方彻底停止呼吸。
我能赢吗?
不能。
可我没有别的路。
——她会被阿勒坦留下。留在白狼帐里,留在那张铺满兽皮的地铺上。他会学会她的语言,她会学会他的沉默。清晨他会把她脚踝那圈骨珠链重新系紧,黄昏她会在帐口等他狩猎归来。
她会成为他的。
不是身体——那具身体早已被太多陌生的手揉捏、太多贪婪的目光舔舐、太多“蓝月”舞台下的醉客用钞票换取片刻虚假的占有。
是别的东西。
是她看他的眼神里那层冰面裂开的第一道细纹。是她昨夜说“阿勒坦”时舌尖碾过每个音节的轻重。是她站在祭台中央、赤裸着淋着雨、却低头望向他空无一人的帐帘——
她在等他来看她。
他没有来。
她的睫毛垂下时,那道阴影里藏着什么?
不是失望。
比失望更软,更脆,更像一枚刚刚成形、还未坚硬的核。
那枚核会生根。会发芽。会长成她再也不能连根拔起的树。
而我。
我还在营地的阴影里劈柴、潜伏、数白狼帐外的守卫脚步从三百次心跳变成二百九十九次。
我来这里是为了带她回去。
可如果她不想回去呢?
这根刺终于扎穿了骨头。
——
第八夜。
我开始在营地散布消息。
不是明目张胆地宣告。是借着炊帐的火光,借着阿云嘎那帮少年嚼干肉时百无禁忌的闲聊,借着女人们在水边捶洗衣物时竖起的耳朵。
“听说新来的牧羊人是从神女来的那个方向来的。”
“听说他每天望白狼帐,望的不是神女,是阿勒坦。”
“听说他以前认识神女。”
“听说——神女是他的女人。”
最后这一句是我自己说出去的。
说出口的那个瞬间,舌底泛起极苦的涩,像吞了一枚未熟透的青柿。
那是我的母亲。
我怎能说她是“我的女人”?
可这是草原。
这里不认母子,不认血缘,不认文明世界里那套用二十年哺育与陪伴织成的、柔软而坚韧的名分。
这里只认占有。
阿勒坦把她抢进白狼帐,她就是他的。除非另一个人宣称自己才是最初的占有者,并用刀锋与鲜血重新确认这份归属。
我说她是我的女人。
这句话像一枚石子投进初冬的湖面。
涟漪很小,却一圈圈荡开。
——
第九夜。
涟漪荡回了我自己。
我正在炊帐后面刮一张羊皮——阿云嘎教我如何用石刀把残肉从皮子内面剔净,说夏天之前攒够十张好皮子,就能换一柄真正的铁刀——忽然察觉帐内的说话声低了下去。
不是彻底安静。
是那种刻意压低的、夹杂着频繁停顿与交换眼神的私语。
“……听说了吗,那个牧羊人……”
“神女是他的女人?”
“他怎么不去找阿勒坦?”
“不敢吧,你看他那身板……”
有人嗤笑了一声。
是男人的声音,粗哑,带着酒后特有的拖腔。
“自己的女人被抢了只敢躲在这儿刮羊皮,算什么男人。”
我没有回头。
石刀在皮子上划出长长一道,差点割破我的虎口。
——
第十夜。
消息传到阿云嘎耳朵里,是从他阿妈那里。
他蹲在我旁边,帮我码晾干的羊皮,忽然低声问:“你那天说的……是真话?”
“哪句?”
“神女是你的女人。”
我没有回答。
他等了一会儿,把一张卷边的皮子用力抻平。
“如果是真话,”他说,“你不该只是说说。”
他的声音很轻,没有责备,像在陈述一件草原上人人皆知的基本规则。
“白狼部的男人不会把属于自己的东西挂在嘴上就算了。他们会握在手里。”
他顿了顿。
“握不住,也要去握。握到死为止。”
我看着他。
十四岁,缺半颗门牙,父亲死在去年冬天。他还没有资格上战场,却已经学会了战场的第一条规则。
我忽然明白他为什么每晚都要抢那块烤焦的肩胛骨。
不是为了肉。
是为了抢。
——
第十一夜。
我在水边遇见那个老阿妈。
她正弯腰捶打一件浸透汗渍的战袍,灰白的辫子垂到水面,随她手臂的动作轻轻摆动。
她看见我。
不是偶然。她在这里等我。
“你就是那个牧羊人。”
不是疑问。
我点头。
她继续捶打战袍。一下,两下,三下。水花溅在她枯瘦的手背上,她像没有感觉。
“神女昨夜问起你。”
我的心脏骤然缩紧。
“她问——那个每天傍晚站在旧帐边的少年,叫什么名字。”
她没有抬头,声音平淡得像在说今夜可能要落雨。
“我没有告诉她。”
她终于抬起眼睛。
那双眼太老了,老到虹膜边缘晕开一圈灰白的雾,老到我无法从那片雾里分辨任何情绪。
“你应该自己去告诉她。”
她把战袍从水里拎起来,拧干,搭在臂弯。
转身。
走了。
我站在原地,脚趾抠进岸边湿软的泥。
她问起我了。
她来到这个世界第十二夜,被拖行、被揉捏、被剥光、被推上祭台当着千百人的面跳那场名为神舞的脱衣舞——她问起我了。
她在白狼帐里,躺在阿勒坦身侧,开口第一句是问那个每天傍晚站在旧帐边的少年叫什么名字。
她没有说“我的儿子”。
她只说“那个少年”。
可她问的是我。
——
第十二夜。
我不能再等了。
不是怕阿勒坦把她占得更深。
是怕我自己。
怕我再这样每天站在旧帐边望着那顶垂落的帘子,把她的身影从记忆里一遍遍捞出来又放回去,放回去又捞出来——我会变成另一种东西。
不是儿子,不是拯救者。
是一个只会在暗处观望、永远不敢走到光里的懦夫。
我走向白狼帐。
不是今夜。
是明天。
明天清晨,当阿勒坦从帐中走出来,去校场点阅他麾下那三百名持矛武士的时候。
我会站到他面前。
用我偷来的这身羊皮,用我学会的这门粗砺语言,用我这副不够强壮、却还能握住刀柄的十六岁躯体。
我会告诉他——
“神女是我的女人。”
“我要与你决斗。”
——
这念头一旦成形,便像吸饱了水的木楔,再也不能从脑髓里拔出。
我开始谋划细节。
决斗的规矩:阿云嘎说,白狼部的决斗不限兵刃,不限手段,只分生死。战场就在营地中央那片祭台前的空地,所有成年男子都必须围观。赢家带走女人,输家被拖进乱葬谷——那里没有坟墓,只有秃鹫与野狼。
我不能输。
可我如何赢?
硬碰硬,十个我也会死。
我需要别的。
关节技。杠杆原理。四两拨千斤。
还有——他不敢杀我的东西。
他如果知道我是她儿子呢?
这念头刚浮起就被我按下去。
不行。
那不是决斗,那是乞求。
草原上没有人会对乞求者手下留情。他只会更加轻蔑,更加确信她应该属于他——而不是属于一个连真实身份都不敢亮明的懦夫。
那么。
我有什么是他没有的?
答案在第十三夜清晨浮出水面。
我在水边洗脸,低头看见自己的倒影——瘦削的下颌,因连日饥饿而凹陷的颊,和那双与母亲一模一样的、眼尾微微上挑的杏眼。
眼睛。
他每次看她时,那双瞳孔深处总有困惑。
他在困惑什么?
他不知道她从哪里来。
不知道她从前穿什么衣服、吃什么食物、用什么语言做梦。
不知道她年轻时爱过什么人,为什么生下孩子,那个孩子如今在何处。
不知道她左乳边缘那颗朱砂痣,是天生就有,还是后来在某具陌生的身体旁被种下。
我什么都知道。
我知道她怕黑,睡觉必须留一盏夜灯。
我知道她十七岁离开家,一个人在南方那座闷热的城市里活了七年才生下我。
我知道她从不告诉我那个人是谁。
我知道她把学费折成小方块塞进中控台缝隙时,指腹会在钞票边缘多停留一秒——那是她在数,还差多少,还差多少,还差多少就能让我离开那座城市。
我知道她看我的眼神,和看任何人都不一样。
那不是女人看男人的眼神。
那是母亲看儿子的眼神。
阿勒坦永远不会有这个。
他永远无法知道她是谁。
而我。
我甚至可以不是她的儿子。
我可以是——
我抬起头,把掌心的冷水拍在脸上。
——可以是她的男人。
这只是决斗需要的身份。
这只是草原规则的漏洞。
这只是我夺回她的手段。
不是吗?
我这样问自己。
水面上的倒影没有回答。
——
第十四夜。
营地开始窃窃私语。
不止是关于“神女是牧羊人的女人”这个传闻。是另一个传闻:牧羊人打算挑战阿勒坦。
我不知道这消息是谁传出去的。也许是阿云嘎,也许是我自己在某个出神的瞬间把心事挂上了眼角。也许是那个老阿妈,她从水边回去后对谁也没说,可她的沉默本身就是最响亮的宣告。
无论如何,传出去了。
收不回来了。
今夜炊帐格外安静。阿云嘎没有抢那块肩胛骨,他把骨头递给我,我摇头,他就自己慢慢啃着,眼睛一直落在我脸上。
“你真的要去?”
我点头。
他沉默了很长时间。
久到篝火添了三次柴,久到帐外最后一个醉酒的武士被同伴架走,久到他那块肩胛骨上的肉丝都被啃得干干净净,露出底下泛黄的骨面。
他把骨头放下。
“你赢不了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那为什么还要去?”
我看着篝火。
火舌在木柴边缘舔舐,把黑色的炭痕一层层覆上金红的纹理。那些纹理很脆弱,风一吹就散成灰烬,飘进帐顶的黑暗里。
“因为她是我的女人。”
我听见自己这样说。
阿云嘎没有再问。
他站起身,拍了拍膝上的灰,往帐口走了几步。然后停住。
“明天清晨,”他没有回头,“我会去看。”
他的背影被帐外更浓的夜色吞没。
——
第十五夜。
今夜无风。
白狼帐外的守卫如期换岗,二十次呼吸的空档,老阿妈从帐后那道兽皮缝补处掀帘出来,拄着木杖,一步一步走向炊帐。
三百次心跳。
我没有数。
我靠在旧帐的阴影里,望着那顶垂落的帘子,把明天要说的话在舌底反复碾磨。
“神女是我的女人。”
不对。太轻了。
“我是来带走她的。”
不对。不够像草原人。
“阿勒坦,我要与你决斗。”
就这一句。
其他的,用刀锋来说。
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。
掌心那道月牙形的掐痕已经结痂,边缘翘起,露出底下新生的粉色皮肤。我用指甲把痂皮一点点剥去,露出那道弯弯的、还未长牢的浅疤。
这是我给她的暗号。
等我把她从白狼帐带出去,穿过营地边缘那片矮灌木,走到我们来时那片原野中央——她会看见这道疤。
她会知道是我。
她会知道她的儿子终于来了。
不是作为懦夫,不是作为只会潜伏在阴影里的观望者。
是作为白狼部规则认可的男人。
是作为——
我没有想下去。
那根刺在骨头里躺了十五夜,今夜忽然不再疼。
不是因为消失了。
是因为它已经长成了骨头的一部分。
——
明天。
我把羊皮裹紧,阖上眼睛。
远处传来一声战马的嘶鸣,在无风的夜里传得很远。
第十六日。
清晨无风。
我醒来时掌心全是汗。
那道月牙形的痂皮昨夜被我剥尽了,新生的浅疤泛着淡粉,在晨光里像一道刚刚愈合的细长刀口。我用拇指反复摩挲那道弧,把它摩得发烫,摩到皮肉深处那根看不见的刺终于完全融进骨血。
该出发了。
我掀开帐幕。
天是青白色的,像一块未经打磨的旧玉。云层压得很低,低到几乎擦着远处那顶镶白狼尾的兽皮帐。炊烟从十几处帐顶同时升起,被无风的清晨凝成一根根笔直的白柱。
阿云嘎蹲在帐外。
他背对着我,正用一根细骨签剔牙缝里残留的干肉丝。听见脚步声,他没有回头,只是把骨签从嘴角换到另一边。
“醒了?”
“嗯。”
“我以为你会跑。”
我没有回答。
他把骨签吐进泥里,站起身,拍了拍膝上的尘土。缺了半颗的门牙在晨光里照成一个黑黢黢的洞,可他没有笑。
“昨晚说的,还算数?”
“算数。”
“如果我死了,”我说,“替我把尸体拖到营地西边那片矮灌木后面。不要埋,不要烧。就放在那里。”
他皱起眉:“那是喂狼。”
“嗯。”
他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你认识那边的人?”
“认识。”
他没有再问。
他只是点了点头,像在确认一桩寻常的交易——我帮你劈了十四夜的柴,你欠我一条命,死后用尸首抵债。
“好。”他说。
我转身往白狼帐的方向走去。
他没有跟上来。
——
营地中央已经聚了人。
不知是谁把消息传出去的——也许是昨夜炊帐里某个竖起耳朵的妇人,也许是今晨挑水时两个武士交换的眼神。总之,当我穿过那排废弃旧帐、踏上祭台前那片圆形空地时,四周已经围了不下百人。
他们自动让开一条路。
不是敬意。是看客对即将赴死之人本能的避让。
我穿过那条人肉砌成的窄巷,脚掌踏在昨夜雨后残留的水洼里,溅起的泥点沾上我的脚踝。
没有人说话。
连孩子都安静了。
祭台还是那块青石,边缘凿痕里还残留着前夜雨水未干的深色湿痕。兽骨旌幡垂在无风的空气里,一动不动。
而祭台后方,那顶镶白狼尾的兽皮帐前,坐着我的母亲。
她坐在一张巨大的、铺了三层厚绒的狼皮座上。
那不是椅子,是整头巨狼的皮毛鞣制缝合而成的坐垫——狼头还保留着,张开的嘴被撑成固定的弧形,露出四枚森白的獠牙,正正枕在她右侧腰窝下。她整个人陷进那片银灰色的厚绒里,像一捧雪落进狼腹。
她穿着另一身祭服。
不是前日跳舞时那件墨色鹿皮。是新的,更短,更少。
上半身几乎只是一条斜裁的窄幅兽皮,从左肩斜斜勒向右腋,在肋侧打了个结。那结系得很松,松到整片左乳几乎完全袒露在晨光里——浑圆,饱满,乳肉顶端那粒淡褐色的朱砂痣像一枚刚点上的印记,在青白的天光下微微发亮。皮料边缘堪堪擦过乳尖,随着她每一次呼吸轻轻刮蹭,把那粒早已挺立的蕊珠刮得更红、更硬。
那条皮料的下缘在她腰侧戛然而止。
整个腰腹都是赤裸的。
她的小腹平坦而柔软,脐窝深深的,像一枚小小的月轮。腹肌纹路在薄薄的皮脂下隐约浮现,随着她屏住的呼吸一道一道绷紧。两侧腰窝深陷成两个小小的涡,涡底泛着细密的汗光,在无风的晨里微微发亮。
下身是一件兽皮短裙——如果那可以叫裙子的话。
那是前后两片极窄的皮料,用筋线松松垮垮缀在腰侧。前面那片堪堪遮住耻骨上缘,露出小腹最下那道浅浅的横弧;后面那片更短,短到她坐进狼皮垫时,整个浑圆硕大的臀峰完全暴露在皮料之外。
那臀太满了。
不是少女那种紧实上翘的弧,是成熟女性特有的、沉甸甸的垂坠与丰盈。两轮雪白的满月被狼皮垫的绒面挤压出更饱满的弧度,臀肉从边缘溢出来,泛着细密的、被粗砺皮料勒出的淡红纹路。她坐得不稳,重心不时在左右臀瓣间轮换,每一次移动都让那片裸露的雪白皮肉轻轻颤动,像刚刚凝住的乳酪。
大腿裸露到根部。
那双腿太长、太直了。从臀峰下缘一路延伸到膝弯,每一寸弧度都饱满得像要化开。晨光照在她大腿内侧那寸极少示人的软肉上,照出一片细密的、被兽皮边缘反复摩擦的淡红。她并拢着腿,膝弯紧紧相贴,脚踝交叠——那是她从前在“蓝月”后巷抽烟时的姿势,是面对陌生目光时本能的自卫。
可在这里,这姿势只让她的身体更暴露。
脚踝上还缠着那圈骨珠链。
她今天穿着鞋。
不是那天遗落在原野里的裸色细高跟——是草原女人穿的软皮短靴,靴口用细筋带交叉绑缚,一圈圈勒过她细白的小腿肚,勒进膝弯下缘那团最软的肉。
而她身旁,坐着阿勒坦。
他今天也换了装束。
不是昨夜那件随意披挂的兽皮袍。他穿着一身崭新的、镶满狼牙的战甲,肩头覆着整块白狼头皮,狼吻正正扣在他额顶,两枚空洞的眼窝朝前凝视。
他坐在她右侧,身形几乎有她两倍宽。他的一只手垂在身侧,另一只手——
另一只手搭在她裸露的腰窝上。
拇指正正陷进那道深涡,指腹一下一下摩挲那片薄薄的皮肉。他的动作很轻,像在抚摸一件易碎的瓷器,又像在反复确认——这是我的。
他的眼睛落在人群里。
落在我身上。
我站在空地中央。
脚掌陷进晨露未干的泥土,脚趾冻得发麻。那件偷来的羊皮裹在身上,领口竖到下颌,露出底下母亲亲手洗过无数次的旧校服领边。
我仰头望着高台上那顶狼皮座。
望着她。
她看见我了。
那一瞬间,她眼底有什么东西骤然裂开。
不是昨夜那道冰面细纹——是整片冰层同时崩碎,露出底下深不见底的黑色湖水。她的瞳孔急剧收缩,睫毛剧烈颤动,腰窝在阿勒坦掌下猛地绷紧,那两轮裸露的雪白臀峰几乎是从狼皮垫上弹起来——
又硬生生压回去。
她没有起身。
她不敢起身。
她只能坐在那里,坐在那个年轻王者掌下,用那双骤然盈满水光的眼睛望着我。
那眼神我太熟悉了。
六岁高烧不退,她三天三夜没合眼——是这样看我。
十二岁被堵在校门口骂“脱衣舞女的儿子”,她冲出来把我搂进怀里——是这样看我。
十六岁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,她坐在“蓝月”后巷的水泥台阶上哭了整整一个小时,抬起脸来——还是这样看我。
可这次不一样。
这次里面多了一样东西。
恐惧。
不是被拖行、被揉捏、被剥光时那种生理性的战栗。是更深的、从骨缝里渗出来的恐惧。
她在怕。
怕我开口。
怕我站在这千百人围观的空地中央,说出那句她不敢听的话。
我望着她。
然后我移开眼睛。
我望向阿勒坦。
他的拇指还停在她腰窝里,可他的视线已经完全落在我脸上。那目光没有轻蔑,没有愤怒——只有困惑。
像昨夜,像前夜,像他第一次用舌尖濡湿拇指去按她唇上血口那一刻的困惑。
他不明白。
这个瘦弱的、连羊皮都穿不好的南边少年,为什么敢站在这里。
我开口。
声音比我想象中更稳。
“阿勒坦。”
营地骤然静下来。静到能听见风穿过旌幡细绳的微响。
“神女是我的女人。”
我把每个字都咬得很慢,慢到它们像一枚枚冰冷的铁钉,钉进这片无风的晨空。
“我要你立刻还给我。”
“按草原的规矩——我们决斗。”
人群里爆发出一阵压抑的嗡鸣。
那嗡鸣像潮水,从空地边缘层层涌向高台,又在高台边缘骤然止息。
阿勒坦没有说话。
他的手还停在她腰窝上,拇指的摩挲却停了。他低头看着她——不是看我,是看她。
他的嘴唇翕动。
“那个男人,”他的声音很低,低到只有她听得见,“是你的主人吗?”
母亲没有回答。
她的嘴唇张了张,又阖上。喉间挤出一声极轻的、像幼兽濒死前的呜咽。她的腰在他掌下剧烈颤抖,那两轮裸露的臀峰在狼皮垫上反复碾磨,磨出细密的红痕。
“他是……”
她说不下去。
阿勒坦没有催。
他只是看着她,瞳孔深处那团困惑的雾越来越浓。
她的眼泪终于落下来。
不是哭泣,是无声的、大颗大颗的泪珠从眼眶滚落,滑过颧骨,滑过下颌,滴进锁骨尽头那粒褐色的小痣。她的胸口剧烈起伏,那片几乎完全袒露的左乳随着呼吸上下弹跳,朱砂痣在泪光里模糊成一粒晕开的樱桃核。
“他不是……”她的声音碎成一片,“他不是我的主人……”
她不敢说我是她的儿子。
她不敢说。
因为她知道,一旦说出那个真相,我就彻底没有机会了。
草原不会把母子认作夫妻。
草原不会为血缘决斗。
她只能否认。
否认我是她的主人,也否认我是她的儿子。
她只能把我变成——一个宣称占有过她的陌生男人。
她的眼泪还在流。
可她的嘴唇终于抿紧了。
阿勒坦看着她。
很久。
然后他收回停在她腰窝上的手。
他站起身。
他的身形太高大了。站起来时遮住了大半片晨光,把我和她之间那道视线彻底切断。我只能看见他肩头那枚白狼头颅,两枚空洞的眼窝正对着我的眉心。
“我接受。”
他的声音很低,很沉,像从深谷里滚上来的巨石。
“明日清晨。祭台前。”
“兵刃自选,生死自负。”
他顿了顿。
“赢家带走她。”
他转身,背对我,重新坐回她身侧。
他的手掌重新覆上她的腰窝。
她没有躲。
她的眼睛越过他的肩头,越过那枚狰狞的白狼头颅,越过这片无风的、凝固的晨空,落在我的脸上。
泪痕还没干。
可她的嘴唇轻轻动了一下。
口型太轻,太快,像蝴蝶振翅。
她说——
“走啊。”
我没有走。
我站在原地,把掌心那道月牙形的浅疤攥进拳心,转身走向人群外围。
人群自动让开一条路。
比来时更宽。
我穿过那条人肉砌成的窄巷,脚掌踏过自己来时踩下的脚印。晨露未干,泥土还软,每一步都陷得很深。
阿云嘎蹲在旧帐边缘。
他看见我,没有站起来。
“明天?”
“明天。”
他把手里那根骨签又塞进牙缝,剔出一丝看不见的肉屑。
“你说要智取,”他没有看我,“智取是什么?”
我把手伸进羊皮内袋。
指尖触到那枚冰凉的金属。
那是一把格洛克17的外形——塑料滑套,金属内胆,三百二十块人民币从同城二手交易网淘来的。射击俱乐部的教练说这玩意儿打钢珠精度不错,就是威力太小,五十米外连汽水瓶都打不穿。
我没有五十米。
祭台到决斗场中心,不超过十五步。
钢珠有十二枚。
我用拇指一粒粒数过。
十二。
够了。
“阿云嘎,”我说,“明天你来观战。”
他抬头。
“如果看见阿勒坦忽然跪下去,”我把气枪塞回内袋,“就去白狼帐后面等我。”
他盯着我的脸。
很久。
“你那是什么东西?”
我没有回答。
他也不再问。
他只是把那根剔了半天的骨签吐进泥里,站起身,拍了拍膝上的土。
“好。”
——
太阳升起来了。
营地从晨光里慢慢苏醒。炊烟重新飘散,战马被牵出马厩,孩子们赤脚踩过水洼。
我靠在那顶废弃旧帐的阴影里,把气枪拆开又装上,装上又拆开。
十二枚钢珠在掌心滚来滚去,像十二粒冰凉的雨滴。
远处白狼帐的帘子掀开一道缝。
老阿妈端着空陶罐出来,一步一步走向炊帐。
三百次心跳。
我阖上眼睛。
明天,一切都在明天决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