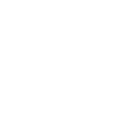7.被迫去灰狼部求雨的妈妈会被强奸吗?
接下来的几天,我慢慢明白了什么叫“王和后”。
起初我以为那只是个头衔,像电影里演的,坐在高处发号施令,等着别人把肉送到嘴边。可真正过起来才发现——那不是享受,那是工作,而且是全天无休的那种。
每天天不亮,帐篷外面就开始有人影晃动。脚步声,低语声,咳嗽声,还有小孩偶尔的哭闹——全从兽皮缝隙里渗进来,像一锅慢慢煮开的水。我总是被这些声音吵醒,可每次睁开眼,第一眼看见的都是她。
她就躺在我身边。
有时候侧着,脸朝向我,呼吸轻轻喷在我脸上,带着夜里积攒的温热。有时候平躺着,长发散得到处都是,像黑色的水草铺在纯白的狼毛上。有时候背对着我,脊柱那道沟从后颈一路滑下去,滑进臀缝里,晨光从帐篷缝隙钻进来,正好照在她身上,把那道沟涂成金色。
每一个清晨,我都会趴在那里,安安静静地看一会儿。
看着她的睫毛在晨光里轻轻颤动,看着她的嘴唇微微张开露出一点点牙齿,看着她胸口的起伏——那两团饱满的乳肉随着呼吸缓缓升起又缓缓落下,像两座沉睡的山丘。
那颗朱砂痣还在那里。嵌在左乳边缘,暗红色的,像一个永远抹不掉的印记。
有时候我会忍不住伸手去摸。很轻,很慢,指腹从她锁骨滑下去,滑过乳肉,滑到那颗痣上,轻轻按一下。
她会醒。
每次都会。
可她从不生气。只是睁开眼,望着我,眼睛在晨光里亮得像两颗洗过的星星。
“又摸?”“嗯。”“几岁了?”“不知道。”她就会笑。然后伸出手,把我揽过去,让我趴在她身上。胸口贴着胸口,小腹贴着小腹,大腿贴着大腿——和第一夜一模一样。
那根东西会自己醒过来。
它会顶在她小腹上,或者滑进她两腿之间,或者直接抵在那个湿润的地方。可她从不急着让它进去。她就那样抱着我,抚着我的背,像哄小孩一样轻轻拍着。
“今天要做什么?”我问。
“昨天说到哪儿了?”“分羊。”“对,分羊。还有灰狼部的人今天要到。”“他们来干什么?”“不知道。”她顿了顿,“来了就知道了。”我们就那样躺着。
很久。
直到外面的声音越来越大,大到不能再装听不见。
她才轻轻拍拍我的屁股。
“起来。王要上朝了。”---“上朝”这个词是我说的。她一开始听不懂,后来听多了,也跟着说。
可这里的“朝”和电视里演的完全不一样。
没有金銮殿,没有龙椅,没有跪了一地的文武百官。只有一个用木头搭起来的大棚,棚顶盖着兽皮,棚底下铺着干草。头人们坐在干草上,普通部落民站在棚子外面,有什么事儿就走进来,跪在中间说。
我就是坐在最里面的那个。
坐在一块垫高的石板上,石板上面铺着狼皮——纯白的,和我帐篷里那片一模一样。她就坐在我旁边,比我矮半个身子,坐在一块小一点的石板上。
第一个来的是那个老得牙都掉光的老头。
他叫阿公。
不是名字,是称呼。整个部落的人都这么叫他,老的叫,小的也叫,连她都叫。阿公走进来,在我面前坐下,干草被他压得窸窣响。
“王,”他说,“羊分完了。”“怎么分的?”“按人头。每家几只母羊几只羔子,都记着呢。”我点点头。
在现代社会,我是个刚考上大学的学生,什么都不懂。可在这里,我是王。我必须懂。
“母羊留多少?”“留了三成。”“够过冬吗?”阿公愣了一下。他抬起头,那双浑浊的眼睛在我脸上转了一圈,然后转向她。
她没说话。
阿公又转回来。
“够。”他说,“往年也是这样。”“往年饿死过羊吗?”“饿死过。”“多少人?”他沉默了。
我知道答案。来的第一天我就知道了——这个部落每年冬天都会饿死人,死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。不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肉,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做储备。他们把秋天多余的羊杀了,肉吃不完就臭掉,到了冬天又没得吃。
“今年别这样。”我说。
“那咋办?”“留六成母羊。羔子也留,挑壮的留,瘦的杀了吃。”阿公的眼睛睁大了一点。
“六成?那草不够吃——”“那就种。”“种?”他完全听不懂。
我看了看她。
她轻轻点了点头。
于是我深吸一口气,开始解释。
解释什么叫草场轮牧,什么叫冬季储备,什么叫把羊粪收集起来开荒种地——种那些从铁门那边换来的种子,种那些我们现代人吃了上千年的东西。
阿公听着。
棚子外面的人也听着。
他们听得很认真,像听天书一样认真。我知道他们多半听不懂,可他们还是听。因为我是王。因为我的话,就是规矩。
讲完了。
阿公沉默了很久。
然后他站起来,弯下腰,脑袋几乎碰到膝盖。
“王,”他说,“圣明。”我不知道这个词是从哪儿来的。也许是以前某个穿越者留下的,也许是这个世界本来就有的。可那两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,落进我耳朵里,让我浑身一震。
他退出去了。
下一个进来的是那个脖子上挂满骨珠的胖女人。
她叫阿姆。
也是称呼。
阿姆管的是交易。
“铁门那边来人了。”她跪在干草上,声音粗得像砂纸磨石头,“想换盐。”“拿什么换?”“皮子。还有茶。”茶。
那两个字像一颗石子投进我心里,激起一圈涟漪。
“什么茶?”“黑黑的,一小块一小块的。他们说叫茶砖。”我心跳忽然快起来。
“拿一块我看看。”阿姆从怀里摸出一个东西,递过来。
我接过来。
那东西巴掌大,黑褐色的,硬得像砖头。我把它凑到鼻子底下闻——一股淡淡的、熟悉的、属于另一个世界的气味钻进鼻腔。
茶。
真的是茶。
我的手微微发抖。
“怎么了?”她问。
我转头看她。
“这是茶。”我的声音有点哑,“我们那个世界的东西。”她的眼睛亮了一下。
“能换吗?”她问阿姆。
“能。一块茶砖换三张好皮子。”“换。”她说,“有多少换多少。”阿姆点点头,退出去。
我握着那块茶砖,半天没说话。
她把手搭在我手上。
“在想什么?”“在想,”我说,“这里离汉人的地盘可能不远。”“汉人?”“我们那个世界的民族。种茶,喝茶,把茶压成砖运到边疆换马换皮子——历史上干了几千年。”她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那又怎样?”我愣了一下。
“什么怎样?”“就算离汉人近,”她说,“我们回得去吗?”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
她也没再问。
只是把手从我手上移开,轻轻拍了拍我的腿。
“下一个。”---那天晚上回到帐篷,我还在想茶砖的事。
她躺在我身边,我趴在她身上——这是我们睡了几天的固定姿势。她说这样舒服,像盖了一床会喘气的被子。我不介意。趴在她身上,听着她的心跳,闻着她的气味,那东西放在她里面——这已经是我的睡眠仪式。
“还在想茶?”她的手抚着我的背。
“嗯。”“想什么?”“想鸡蛋。”我说。
她笑了一下。
“鸡蛋?”“茶叶蛋。”我说,“用茶砖煮的,加盐,加酱油,煮很久,蛋壳裂开,花纹渗进去——可好吃了。”“你吃过?”“小时候吃过。学校门口有卖的,五毛钱一个。”她沉默了一会儿。
然后她轻轻动了动,把我从她身上推下来,让我侧躺在她身边。她翻身面对着我,手搭在我腰上。
“明天试试。”“试什么?”“煮茶叶蛋。”她说,“有茶,有盐,有蛋。就差酱油。”“酱油呢?”“找。这个部落没有,铁门那边可能有。或者我们自己酿。”我望着她。
帐篷里很暗,只有一线月光从顶上缝隙漏下来,照在她脸上。她的眼睛很亮,亮得像两颗浸在月光里的珠子。
“你认真的?”“嗯。”“可是——”“可是什么?”我张了张嘴。
我想说可是我们穿越了,可是我们在一个陌生的世界,可是我们是王和后,可是有太多事要做——可那些话到了嘴边,全堵住了。
因为她的眼睛在笑。
那种笑,我太熟悉了——蓝月后巷的晚上,出租屋的厨房,她喝醉了数星星的时候——都是这样的笑。
那笑容在说:管它呢。
管它穿越不穿越,管它王不王后,管它什么大事小事——我想吃茶叶蛋,那就煮茶叶蛋。
就这么简单。
我忽然也笑了。
“好。”我说,“明天找酱油。”她伸出手,把我揽过去。
我又趴回她身上。
那根东西在她里面待了一整天,软着,温着,被她的肉壁轻轻含着。此刻它又开始醒过来,慢慢抬头,慢慢胀大,把她里面撑开。
她的呼吸变了一下。
“又来了?”“嗯。”“这几天太密了。”“我知道。”“明天还有事。”“我知道。”“那你还来?”我没说话。
只是把脸埋在她颈窝里,深吸一口气。她的气味灌进来——晚香玉的残香,汗水的咸,还有从她身体最深处渗出来的、混着那东西气味的甜腥。
她的手抚着我的后脑勺。
“算了。”她的声音很轻,“反正你是王。”“王怎么了?”“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”我抬起头,望着她。
月光照在她脸上,把她的轮廓勾成一道淡淡的银边。她的眼睛弯着,嘴角弯着,整张脸都在笑。
“那王后呢?”我问。
“王后怎么了?”“王后想干什么?”她伸出手,手指按在我嘴唇上。
那道血痂已经掉了,可她的指腹按在那里,还是有一点痒。
“王后想看着王高兴。”她说。
我张开嘴,把她的手指含进去。
她轻轻笑了一声。
然后她的大腿夹紧我的腰,把我往下一拉——那根东西滑进去,滑到最底。
耻骨抵着耻骨,小腹贴着小腹,胸口贴着胸口。
没有缝隙。
“睡吧。”她的声音从头顶传来。
我闭上眼睛。
手指还含在嘴里。
那根东西还在她里面跳。
一下,一下。
像心跳。
---几天后,灰狼部的人来了。
那天早上我刚处理完一批羊的分配问题——按照我说的,留了六成母羊,杀了四成羔子,肉分给各家各户腌制起来,皮子送去硝制,骨头留着熬汤。部落里的人看我的眼神变了。不是刚来时那种审视的、怀疑的、像看外来者的眼神。是一种软的、热的、带着一点点崇拜的眼神。
阿公说,从没见过秋天这么丰盛。
阿姆说,铁门那边的人听说了,想多换些肉干。
连那些平时不怎么说话的女人,也开始主动给我送东西——一小碗熬得浓浓的羊奶,一块烤得焦香的肋排,一把刚摘的野果子。
她们跪在我面前,把东西举过头顶。
我叫她们起来。
她们不起来。
我只好接过来。
然后她们就笑,露出被肉和奶滋养得饱满的脸,转身跑开。
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她就坐在旁边,看着这一切。
“你笑什么?”“没笑什么。”“你明明在笑。”“我在想,”她说,“你现在是真正的王了。”“什么意思?”“她们看你的眼神,”她顿了顿,“和看我一样。”我没听懂。
她也没解释。
就在这时,远处传来一阵喧哗。
马蹄声。很多马蹄声。
我站起来,朝声音的方向望去。
营地入口那边,烟尘滚滚。烟尘里隐约可见一群骑手——骑着那种矮小结实的草原马,马背上驮着人,人的背上背着弓,腰间挎着刀。
灰狼部。
阿公走到我身边,那双浑浊的眼睛眯起来。
“是灰狼部的头人。”他说,“赫连。”“赫连?”“草原上最狠的角色。”阿公的声音很轻,“去年杀了自己亲弟弟,因为弟弟想抢他的位置。”我点点头。
心脏跳得快了一点。
不是因为怕。是因为第一次见别的部族的头人——第一次真正面对这个世界的规则。
那群骑手越来越近。
我看见了最前面那个。
他骑着一匹纯黑的马,马的额头上有一道白纹,像一道闪电。他本人比后面那些骑手都高,肩膀宽得像一扇门板,脸被草原的风吹得黝黑,颧骨突出,眼睛细长,像两把开了刃的刀。
他身后跟着二十多个骑手。
全是精壮的汉子,腰里别着刀,背上背着弓,马鞍旁挂着血淋淋的猎物——几只野羊,一只鹿,还有一头我不知道名字的野兽。
他们在营地入口勒住马。
灰尘落下去。
赫连坐在马上,居高临下地望着我们。
望着我。
“白狼部的新王?”他的声音很粗,像石头在石头上磨。
“是我。”他从马上跳下来。
落地的时候,地上的土被他踩得陷下去一小块。他朝我走过来,一步一步,每一步都踩得很实,像钉子钉进地里。
走到我面前三步远,他停下来。
打量我。
从上到下,从下到上。
然后他笑了。
那笑容很难看——嘴角扯开,露出一口被肉和血染得微微发黄的牙齿,眼睛却还细着,像两条缝。
“比我想的嫩。”他说。
我没说话。
他的目光从我身上移开,移到我身后——移到她身上。
停住了。
那目光变了。
不是方才那种审视的、傲慢的、像看小孩的目光。是另一种东西。直的。硬的。带着某种原始野性的、像狼看见猎物时的光。
“这就是神女?”我没回答。
可她站了出来。
走到我身边,和我并肩站着。
“是我。”赫连的眼睛眯得更细了。
“我听过你的名字。”他说,“铁线。”铁线。
那是她的名字——至少在蓝月的时候,她是用这个名字的。我不知道她怎么把这个名字带到这个世界,也不知道这些人怎么知道的。可她站在那里,迎着赫连的目光,脸上没有一丝波澜。
“我也听过你的名字。”她说,“赫连。灰狼部的头人。去年杀了自己弟弟。”赫连的脸色变了一下。
只是一下。
很快又恢复成那副傲慢的样子。
“杀弟弟怎么了?”他说,“他该死。”“我没说不对。”赫连愣了一下。
“那你什么意思?”“我只是确认一下。”她说,“确认我有没有认错人。”赫连盯着她。
很久。
然后他笑了。
这回的笑和刚才不一样。刚才的笑是冷的,是嘲讽的,是居高临下的。这回的笑里,带着一点点——我说不上来——也许是欣赏,也许是好奇,也许是别的什么。
“有意思。”他说,“白狼部不光换了个嫩王,还多了个会说话的婆娘。”“她是我妻子。”我说。
赫连的目光转回来。
落在我脸上。
那目光像两把刀,从我眼睛扎进去,一直扎到后脑勺。
“我知道。”他说,“我就是为她来的。”我的心跳停了一拍。
“什么意思?”赫连往前走了一步。
就一步。
可那一步让我浑身汗毛竖起来——因为他的手已经按在刀柄上。
“草原上都在传,”他说,“白狼部的新王娶了神女。神女跳的舞能求来雨。你们白狼部今年雨水比往年多三成,草长得比人高,羊肥得走不动路。”他顿了顿。
“我们灰狼部今年旱了。”我的手攥紧。
攥得很紧。
指甲掐进肉里,掐得生疼。
“所以?”“所以我来借神女。”赫连说,“借几天。让她给我们灰狼部也跳一场。求一场雨。”“不行。”那两个字是从我嘴里蹦出来的。
蹦得太快,快到我自己都没反应过来。
赫连的眼睛眯起来。
那两条缝里射出的光,比刚才更冷,更硬,更像刀。
“你说什么?”“我说不行。”赫连的手把刀柄握紧了。
他身后那二十多个骑手也动了。不是下马,是把手按在刀柄上——二十多只手,二十多把刀,齐齐按着,只等一声令下。
气氛一下子绷紧。
绷得像拉满的弓。
营地里的白狼部人也围过来。男人站在前面,女人和孩子退到后面,可他们没有跑,没有躲,只是站在那里,望着我。
等着我说话。
我深吸一口气。
“她是我的妻子。”我说,“不是借的东西。”“我知道她是你妻子。”赫连说,“我没说要抢。我说借。借几天。还回来。”“借也不行。”“为什么?”“因为——”我顿住了。
因为什么?
因为她是我的母亲?因为在这个世界她只是我的妻子?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解释神女和求雨这件事根本就不存在?
我张了张嘴。
什么也说不出来。
赫连盯着我。
那目光里渐渐浮起一层嘲讽。
“因为什么?”他重复,“因为舍不得?因为新婚没几天,舍不得让婆娘离开自己帐篷?”周围响起几声低笑。
来自他身后那些骑手。
我的脸烫起来。
不是因为羞。是因为怒。
可我不知道怎么反驳。
因为他说的是事实。我确实舍不得。舍不得她离开我的帐篷,舍不得她离开我的视线,舍不得她离开我的身体——哪怕只是一天。
就在这时,一只手搭在我手上。
她的手。
我转头看她。
她望着我。
那双眼睛很平静。平静得像一潭深不见底的水。
“让我和他谈。”她说。
“可是——”“让我谈。”她的声音很轻,却不容置疑。
我松开手。
她往前走了一步。
面对着赫连。
“你说借我,”她说,“借几天?”赫连愣了一下。
显然没想到她会这么问。
“三——三天。”他说,“三天够了。”“三天之后呢?”“还回来。完完整整还回来。一根头发不少。”“你拿什么担保?”赫连又愣了一下。
“担保?”“对。担保。”她说,“你借我走三天。万一你到时候不还呢?万一你把我扣下当你的婆娘呢?万一你杀了你的弟弟,再多杀一个外人的丈夫,把我留在灰狼部呢?”赫连的脸变了。
变得很难看。
“你——你什么意思?”“我的意思很明白。”她的声音还是那么平静,“白狼部和灰狼部没打过仗,可也没结过盟。你是外族人,我是神女。你空口白牙说借三天,我就跟你走?万一你骗我呢?”赫连盯着她。
盯着很久。
然后他忽然笑了。
这回的笑和之前都不一样。不是嘲讽,不是欣赏,是——无奈。
“好一张利嘴。”他说,“难怪能当神女。”“所以呢?”“所以你想要什么担保?”她想了想。
“你留下一个人。”“谁?”“你儿子。”赫连的脸彻底变了。
变得铁青。
“你怎么知道我有儿子?”“草原上都知道。”她说,“赫连有七个儿子。最小的那个今年七岁,是你最疼的那个。你到哪儿都带着他。”赫连沉默了。
很久。
然后他转身,朝那群骑手走过去。
走到一匹马前面,伸手从马背上拎下来一个人。
那是个小孩。
七八岁的样子,瘦瘦小小的,穿着一件小号的皮袍,头发扎成几根小辫,脸上还带着没擦干净的鼻涕。他被赫连拎着后领,悬在半空,两条小腿乱蹬,嘴里喊着什么我听不懂的话。
赫连拎着他走回来。
把那小孩往地上一放。
“他。”赫连说,“我儿子。留在这儿。三天后我来接他。接他的时候,把神女还回来。”小孩站在地上,仰着脸望着赫连,又望着我们,眼睛里全是惊恐。
我想说什么。
可她抢先开了口。
“好。”那一个字像一颗石子,投进这片沉默的水潭里,激起一圈涟漪。
赫连盯着她。
“三天。”他说,“就三天。三天后我来接人。如果神女少一根头发——”他顿了顿。
“我就带人来。”他没说带人来干什么。
可他手按在刀柄上,那意思谁都明白。
她点点头。
“三天。”她说,“你儿子会好好的。”赫连又看了她一眼。
那一眼很长。
然后他转身,朝那群骑手走过去。
翻身上马。
马鞭一挥。
那群骑手跟着他,马蹄声隆隆响起,烟尘滚滚卷起,朝营地外面冲去。
越来越远。
越来越小。
最后消失在远处的丘陵后面。
我站在原地。
望着那团渐渐散去的烟尘。
她的手又搭上来。
搭在我手上。
“进去吧。”她说。
我转头看她。
她的脸很平静。平静得像什么都没发生。
“你——”“进去说。”她拉着我的手,朝帐篷走去。
身后,阿公的声音响起来。
“散了散了!没事了!该干嘛干嘛!”人群慢慢散开。
窃窃私语像潮水一样涌起来。
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。
可我能感觉到——那些目光又变了。
不是之前那种崇拜的、软的、热的。是一种新的东西。复杂的。我说不上来。
帐篷帘子放下来。
隔绝了所有目光。
她转过身,面对着我。
“想问什么?”“你疯了?”我的声音压得很低,低到发抖,“拿自己换那个小孩?”“他没疯。”她说,“他真会带人来。”“那你还——”“所以才要留下他儿子。”我张了张嘴。
什么也说不出来。
她望着我。
那双眼睛很亮。
“三天。”她说,“这三天,你要做一件事。”“什么?”“让部落里的人看见你在做事。”她说,“分配牛羊,开垦荒地,交易皮货——什么都行。就是不能待在帐篷里等我。”“为什么?”“因为你是王。”她说,“王不能在王后离开的时候什么都不干。那会让人觉得你离不开女人。”“我本来就离不开——”“我知道。”她伸出手,抚上我的脸。
“我知道你离不开我。”她的声音很轻,“我也离不开你。”“那你还——”“因为只有这样,”她说,“才能不打架。”我沉默了。
她说的对。
可我还是难受。
那股难受从心底涌上来,涌到眼眶里,烫得我眼睛发酸。
她看见了我的眼睛。
她的手从我脸上滑下去,滑到脖子,滑到胸口,滑到小腹——停在那里。
隔着袍子,按着那根东西。
“三天。”她说,“忍一忍。”我的喉咙发紧。
“忍不住呢?”她轻轻笑了一下。
那笑容很短,却暖得像初春的太阳。
“忍不住也得忍。”她说,“因为我不会让别人碰我。”她顿了顿。
“一根头发都不会。”我望着她。
望着很久。
然后我把她拉进怀里。
抱得很紧。
紧到能感觉到她的心跳——咚,咚,咚——隔着两层袍子,从她胸口传过来,和我的心跳撞在一起。
她把脸埋在我胸口。
手还按在我小腹上。
我们就那样抱着。
很久。
帐篷外面,那小孩的哭声隐隐约约传进来。
他被留下了。
被自己的父亲留下当担保。
换她离开三天。
帐篷帘子放下来之后,外面那些声音就远了。
那小孩的哭声,阿公布置人手的吆喝声,女人们窃窃私语的嗡嗡声——全都隔在那层薄薄的兽皮外面,像另一个世界的事。
这个世界里只剩我们两个。
她站在我面前,仰着脸望着我。
那双眼睛在昏暗里很亮,亮得像两点浸过油的灯芯。睫毛很长,尖端微微翘起,每一根都清晰可见。鼻梁直而秀气,鼻尖上沁着一点点细密的汗珠。嘴唇饱满,微微张开,露出一点贝齿,唇色比平时更红——那是刚才在外面说话时自己咬的。
我抬起手。
手指从她额角滑过,把她额前被汗黏住的碎发拨到一边。她的头发很软,很黑,像上好的丝绸,从指尖滑过的时候带着一点点凉意。
她没动。
只是望着我。
我的手从她额角滑下去,滑过眉骨,滑过眼睑,滑过颧骨,滑到下巴。她的脸很小,小到我能一只手捧住。掌心贴着她的下颌,指腹按在她耳垂下面那寸最嫩的皮肤上,能感觉到脉搏在跳——咚,咚,咚——和我的心跳一样快。
“三天。”她说。
“嗯。”
“就三天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她的眼睛弯了一下。
那笑容很短,却暖得像刚煮好的羊奶,从眼睛里溢出来,流进我眼睛里,烫得我眼眶发酸。
“你会想我吗?”
“会。”
“多想?”
我把她拉进怀里。
没有回答。
因为不知道怎么回答。想这种事,能用话说清楚吗?能说多疼吗?能说多痒吗?能说一想到她要离开这张帐篷、离开这张地铺、离开我的身体,胸口就像被人挖走一块那么空吗?
不能说。
只能抱。
抱得很紧。
紧到能感觉到她的心跳隔着两层袍子传过来,和我的心跳撞在一起,咚、咚、咚,像两匹并排奔跑的马,蹄子同时落在地上。
她的脸埋在我胸口。
呼吸透过袍子渗进来,温热的,痒痒的,一下一下喷在我心口那寸皮肤上。
她的手环在我腰后。
十指交叠,掌心贴着我的尾椎骨,轻轻按着。
我们就那样抱着。
很久。
久到外面的声音彻底静下去,久到那小孩的哭声变成偶尔的抽噎,久到天色又暗了几分——那一线从帐篷顶缝隙漏下来的光慢慢移动,从地铺中央移到了帐角,照在那只大陶罐上,把罐口镀成一道金边。
她先动的。
不是推开我,是把脸从我胸口抬起来。
仰着脸望着我。
“去灰狼部,”她说,“就是跳个舞而已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帮他们求雨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她顿了顿。
那双眼睛在我脸上转了一圈,像在找什么。
“你不担心?”
“担心什么?”
“担心——”她停了一下,“担心他们对我做什么。”
我没说话。
因为我知道她要说什么。
她见我不答,自己往下说。
“这个年代的人,”她的声音很轻,“有生育崇拜。觉得男女交合很神圣。求雨的时候,有时候——”
她没说完。
可我知道。
我知道她想说什么。
我抬起手,又抚上她的脸。
“我知道。”我说。
她望着我。
那目光变了。不是方才那种试探的、小心翼翼的、怕我难受的目光。是一种更深的、更软的、带着一点点我看不懂的东西的目光。
“你不介意?”
我想了想。
想了很久。
然后我开口。
“介意。”我说,“怎么可能不介意?”
她的睫毛颤了一下。
“可是——”
“可是我更想要你回来。”
那话从嘴里说出来,比我想的容易。原以为会很疼,会像拔牙一样,每说一个字都扯着神经疼。可真正说出来的时候,才发现没那么疼。
也许是已经疼过了。
从赫连说出“借神女”那三个字开始,从她答应留下那个小孩开始,从那二十多把刀同时按在刀柄上开始——就已经疼过了。
疼到现在,只剩下一种木木的、钝钝的、像被什么东西压着的麻木。
“只要你能回来,”我说,“别的事,我都能接受。”
她望着我。
望着很久。
然后她的眼眶红了。
不是那种要哭的红,是那种忍着的、憋着的、把什么东西拼命往下咽的红。眼睛还是亮的,可那亮里面多了一层水光,薄薄的,像冬天早上结在草叶上的霜。
“你长大了。”她说。
那四个字很轻。
轻得像一声叹息。
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只是把她重新拉进怀里。
抱得更紧。
她的脸又埋在我胸口。这回她没说话,只是呼吸,一下一下,透过袍子喷在我心口。那呼吸比刚才重,带着一点点颤抖,像在忍什么。
我的手抚着她的背。
从肩胛骨滑到腰窝,从腰窝滑到尾椎,又滑回去。一下,一下,很慢,很轻,像她平时抚我那样。
过了很久。
她把脸抬起来。
眼眶还是红的,可那层水光已经褪下去。眼睛重新变得很亮,亮得像两颗洗过的星星。
“还有一件事。”她说。
“什么?”
“这几天,”她顿了顿,“是我的危险期。”
那两个字像两粒冰珠子,落进我耳朵里,冰得我一个激灵。
危险期。
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。
在这个世界,没有避孕药,没有安全套,没有那些现代人用了几十年的东西。男人和女人在一起,就会生孩子。危险期的时候,最容易怀上。
“如果——”她的声音顿了一下,“如果他们真的对我做什么,如果——”
她没说完。
可我知道。
“有可能怀上。”我说。
她点点头。
那动作很轻,轻得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。
我望着她。
她也望着我。
很久。
然后我开口。
“那就给我也生一个。”
她的眼睛睁大了一点。
“什么?”
“我说,”我的声音比刚才稳,稳得像石头,“如果他们真让你怀上,你就补偿我。给我也生一个。”
她愣住了。
整个人愣在那里,像一尊雕像。眼睛睁得大大的,嘴微微张开,睫毛一动不动,连呼吸都停了。
我看着她愣住的样子。
忽然觉得有点想笑。
“怎么了?”
“你——”她的声音有点哑,“你是认真的?”
“嗯。”
“你不觉得——不觉得脏?”
“脏什么?”
“别人的种,”她说,“进到我肚子里,再给你生孩子——你不觉得脏?”
我想了想。
想了很久。
然后我摇头。
“不觉得。”
她的眼眶又红了。
这回是真的红,红得像要滴出血来。那层水光又浮起来,比刚才更厚,更亮,像随时都会溢出来。
“为什么?”她的声音发颤。
“因为是你。”我说,“只要是从你肚子里出来的,就是我的孩子。”
那话说完,她整个人扑进我怀里。
扑得很用力,用力到我后退半步才站稳。她的脸埋在我颈窝里,手臂箍在我背上,箍得死紧,紧得我几乎喘不过气。
然后我感觉到了。
温热的。
一滴。
两滴。
三滴。
滴在我颈窝里,顺着皮肤往下淌,淌进领口,淌到锁骨,淌到胸口。
她在哭。
没有声音的哭。
只是肩膀轻轻抖着,只是呼吸又重又急,只是那些温热的液体一滴接一滴落下来,落在我的皮肤上,烫得像刚烧开的水。
我抱着她。
什么都没说。
只是抱着。
手抚着她的背,一下一下,从肩胛骨滑到腰窝,从腰窝滑到尾椎,又滑回去。
很久。
她抬起头。
满脸的泪痕。眼睛红得像兔子,鼻子红得像小丑,睫毛黏成一缕一缕的,脸上亮晶晶的全是泪。她抬起手,用袖子胡乱擦了一把,把那张脸擦得更花。
然后她笑了。
那笑容和平时不一样。不是宠溺的,不是调侃的,不是那种母亲看孩子式的温柔。是一种我说不上来的笑——又哭又笑,像个小女孩。
“傻子。”她说。
“嗯。”
“大傻子。”
“嗯。”
“天底下最大的傻子。”
“嗯。”
她笑出了声。
那笑声还带着哭腔,沙沙的,哑哑的,在昏暗的帐篷里轻轻回荡。她笑着笑着,又扑进我怀里,把脸埋在我胸口。
这回没哭。
只是埋着。
很久。
然后她抬起头。
踮起脚。
吻住我。
那个吻和之前所有的吻都不一样。不是浅尝辄止的啄吻,不是睡前安抚的轻吻,不是交合时情动深处的深吻。是另一种东西——更慢,更软,更像要把什么东西刻进骨头里。
她的嘴唇贴着我嘴唇。
很软。
软得像两瓣熟透的果子,轻轻一碰就要化开。她的舌尖抵着我齿缝,慢慢往里探,探进来,碰到我的舌头。没有急切地纠缠,只是轻轻碰着,一下一下,像在确认什么。
我的舌头也动起来。
缠住她的。
很慢。
很轻。
她的气息全灌进我鼻腔——晚香玉的残香,汗水的咸,眼泪的涩,还有从她身体最深处渗出来的、那种让我头晕的甜腥。
我搂着她的腰。
她的手插在我头发里。
我们就那样吻着。
很久。
久到嘴唇发麻,久到舌头发酸,久到外面的天色彻底暗下去——那一线从帐篷顶缝隙漏下来的光已经完全消失,只剩下黑暗,浓稠的、温热的、只有我们两个人呼吸的黑暗。
她先分开的。
不是推开,是慢慢往后撤。
嘴唇分开的时候,发出一声极轻的声响——啵。像软木塞从瓶口拔出来的声音,和那天早上那根东西从她里面滑出来时一模一样。
她的额头抵着我额头。
鼻尖碰着鼻尖。
呼吸交缠在一起。
“我该走了。”她的声音很轻。
我没说话。
只是搂着她。
她又等了一会儿。
然后轻轻挣开我的手。
退后一步。
两步。
站在昏暗里,望着我。
我看不清她的脸,只能看见一个轮廓——肩的圆润,腰的纤细,臀的饱满,腿的修长。全在那层薄薄的兽皮底下,若隐若现。
她转过身。
朝帐帘走去。
走到帐帘前,她停下来。
没回头。
“等我回来。”
那四个字从黑暗里传过来,落进我耳朵里,像四颗温热的糖。
然后帐帘掀开。
外面的光涌进来——是火把的光,橘红色的,跳跃着的,照得她浑身都镀上一层金。
她走出去。
帐帘落下来。
黑暗重新把我吞没。
我站在原地。
很久。
然后我走到地铺边上,坐下来。
坐在她睡过的那片地方,那片被她的体温和气味浸透了的纯白狼毛上。我把脸埋进去,深吸一口气。
她的气味还在。
晚香玉的残香,汗水的咸,还有从她身体最深处渗出来的甜腥。
全在。
我趴下去。
趴在她睡过的位置上,把脸埋在她枕过的狼毛里。
闭上眼睛。
——
我不知道自己趴了多久。
也许是一刻钟,也许是一个时辰。黑暗里没有时间,只有她的气味,越来越淡,淡到我几乎闻不出来。
然后外面传来声音。
马蹄声。
很多人。
我站起来。
走到帐帘边上。
掀开一条缝。
外面很亮。火把插在营地各处,把整片空地照得像白天。空地上站满了人——白狼部的人,还有那些灰狼部的骑手。马在喷气,蹄子刨着地,火把噼啪响。
她站在人群中间。
站在赫连面前。
赫连已经上了马,骑在那匹纯黑的、额头上有一道白纹的大马上。他朝她伸出手。
她抬起手。
握住他的。
赫连一用力,把她拉上马。
拉到他身前。
坐在他怀里。
我的心跳停了一拍。
因为那个姿势——她坐在他前面,背贴着他胸口,他的两只手臂从她身侧伸过去,握着缰绳,把她整个人圈在怀里。那姿势太近了,近到她的后背贴着他的前胸,近到她的臀贴着他的小腹,近到——我能看见他的手。
他的手握着缰绳,可握着握着,就松开了。
松开一只。
落下去。
落在她腰上。
隔着那层薄薄的兽皮袍子,按在她腰侧。
她没有动。
赫连的手在她腰上停了一会儿,然后慢慢往下滑。
滑过腰窝。
滑到臀上。
停在那里。
她的臀很大。
即使穿着袍子也遮不住——两瓣浑圆的肉,把袍子撑得紧绷绷的,从腰侧溢出来,圆鼓鼓的,像两座小山。赫连的手掌贴在上面,五指张开,按着那团肉,轻轻捏了一下。
她还是没动。
我的指甲掐进掌心里。
掐得生疼。
赫连的手在她臀上揉了一会儿,然后移开。
移到她大腿上。
她的腿很长。
袍子只到膝盖上面,膝盖以下全露在外面——两截白生生的、细得像藕节似的小腿,在火光里泛着象牙般的光泽。可赫连的手没摸小腿,他摸的是大腿——从膝盖往上,隔着袍子,一寸一寸往上摸,摸到袍子底下,摸到那截被袍子遮住、却遮不完全的、白得像雪的腿根。
她的身体僵了一下。
只是一下。
很快又放松。
赫连的手在她腿根处停了一会儿,然后抽出来。
重新握住缰绳。
她坐在他怀里,一动不动。
火光跳跃着,照在她脸上。
那张脸很平静。平静得像什么都没发生。可我能看见——她的眼睛望着前方,望着营地外面的黑暗,望着那团火光照不到的地方。那眼睛里没有恐惧,没有愤怒,只有一种我说不上来的东西。
空的。
像一潭深不见底的水。
赫连低下头。
凑到她耳边。
说了句什么。
她没回答。
赫连笑了一下。
那笑声从人群那边传过来,粗的,哑的,带着某种满足的意味。
然后他扬起马鞭。
马鞭落下。
那匹黑马长嘶一声,往前冲出去。
她坐在他怀里。
随着马的动作颠簸着。
那两瓣浑圆的、被袍子紧紧裹着的臀,在马背上一下一下地颤,像两团刚揉好的面,被人用手拍着、颠着、揉着。袍子下摆掀起来,露出一大截大腿——白得刺眼,在火光里一闪一闪,像两条刚从奶里捞出来的鱼。
还有更上面的。
臀的底部。
那两团肉和腿根交界的地方,在马背上一颠一颠,露出一小片——只是一小片——白得几乎透明的皮肤,在火光里闪了一下,又缩回去,又闪一下,又缩回去。
像在招手。
又像在告别。
那群骑手跟上去。
马蹄声隆隆响起。
烟尘滚滚卷起。
火把的光被烟尘遮住,越来越暗,越来越远。
最后什么都看不见了。
只有黑暗。
只有马蹄声渐渐远去,渐渐消失,最后变成一片死寂。
我站在帐帘后面。
很久。
然后帐帘被人从外面掀开。
是阿公。
他那张满是皱纹的脸在火光里忽明忽暗,那两颗仅剩的牙齿露出来,黄得像陈年的骨头。
“王,”他说,“那孩子安排好了。”
我点点头。
没说话。
他望着我。
那双浑浊的眼睛在我脸上转了一圈。
“王后不会有事的。”他说,“神女有神保佑。”
我还是没说话。
他又站了一会儿。
然后放下帐帘,退出去。
黑暗重新把我吞没。
我走回地铺边上。
坐下来。
坐了很久。
然后我躺下去。
躺在她睡过的位置上。
把脸埋在她枕过的狼毛里。
深吸一口气。
她的气味已经很淡了。
淡到几乎闻不出来。
可我还是闻。
闻了很久。
直到那股气味彻底消失,只剩下狼毛本身的、带着一点点膻的、干燥的腥气。
我闭上眼睛。
睡不着。
可我也不想起来。
就这样躺着。
等着。
三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