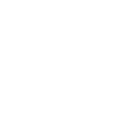11.让作为神女的妈妈去劝降黑狼部
马蹄声又响了三天。
三天里,我们走过那片金色的草原,走过那条我们来时走过的路,走过那些我曾经趴在地上、一寸一寸往前爬过的草丛。那些草还立着,那些土还干着,那些风还吹着——可一切都不一样了。
我怀里抱着她。
她靠着我的胸口,有时候睡,有时候醒,有时候望着那片永远也跑不到头的草原发呆。她的身体已经不抖了,那根一直绷着的弦也松了,可她还是喜欢这么靠着,喜欢让我抱着,喜欢把手握在我的手里,握得紧紧的。
那双手洗干净了。
那天在河谷里,她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。那些吻痕还在,那些抓痕还在,那些牙印还在——可那些污渍没了,那些血没了,那些赫连留下的东西全没了。她洗的时候,我也洗了。把那身干了的血痂洗掉,把那些从赫连身上溅过来的血洗掉,把自己洗成刚来草原时那个样子。
可我们都不是刚来时的样子了。
刚来时,她是神女,我是外来人。刚来时,我们得假装不认识,得叫她“神女”,即使我杀了阿勒坦,夺下白狼部的王位,部族的人也只得叫我“王”。刚来时,我们连说话都得小心,连眼神都得藏着,连晚上都不敢睡在一个帐篷里。
现在不用了。
现在她是王后。我是王。现在整个白狼部都知道——她是我的女人,我是她的男人。现在我们可以光明正大地抱着,牵着,靠着,睡在一个帐篷里。
可我们还是得小心。
小心什么?
小心那五万帐。
小心那两万能打仗的勇士。
小心那个叫灰狼部的、死了首领却还没死透的部落。
赫连死了,可他还有七个儿子。最大的十五岁,最小的还在吃奶。那七个儿子不会一起报仇——阿公说得对,他们会自己打起来,会自己抢位置,会自己杀得头破血流。可等他们打完了,等那个最狠的活下来了,他就会来找我们。
会来找我们报仇。
会来杀我们的人。
会来抢我们的女人。
会来——我不怕。
我怀里抱着她,就不怕。
可我不能不怕。
因为她。
因为她是我的女人。
因为我不想让她再被抢走一次。
所以我要做一件事。
做一件从杀了赫连那天晚上就开始想的事。
———第三天傍晚。
我们回到了白狼部。
远远地,就看见那片营地。那些帐篷还立着,那些火把还燃着,那些人还活着——活着等我们回来。
阿公站在营地门口。
拄着那根比他自己还高的拐杖,站在那片被夕阳照成金色的空地上。他身后站着阿姆,站着那些没跟我们去的老人和孩子,站着那些妻子和母亲——她们的男人跟我们去了,去了四百七十三个,回来四百七十三个,一个没少。
马蹄声近了。
更近了。
近到能看清那些脸。
阿公的眼睛瞪大了。
他看见了什么?
看见了那四百七十三个骑手,一个不少?
看见了那抢来的三百多匹灰狼部的马?
看见了那些驮在马背上的、从灰狼部营地抢来的东西——皮子,铁器,粮食,还有女人?
不。
他看见的是我怀里抱着的她。
是王后。
是那个被赫连抢走、我以为再也见不到、可我现在抱着回来的女人。
阿公的嘴唇哆嗦起来。
那两颗仅剩的、黄得像陈年骨头的牙,在夕阳下一闪一闪。
我勒住马。
抱着她下马。
站在阿公面前。
站在那片被夕阳照成金色的空地上。
阿公望着我。
望着我怀里的她。
然后他开口。
“王后——回来了?”那五个字从他那没牙的嘴里出来,颤颤的,抖抖的,像怕问错了。
我点头。
“回来了。”那三个字从嘴里出来,很轻。
可重得像山。
阿公的眼睛湿了。
那个老得走路都要拄拐杖的老头,那个见过三十年风霜、见过无数生死、见过太多人被抢走再也没回来的老头——此刻站在夕阳里,站在我面前,站在她面前,眼睛湿了。
他没让那泪掉下来。
可那湿在那儿,亮晶晶的,在夕阳下一闪一闪。
他身后,那些女人开始哭。
不是嚎啕大哭——是那种憋着的、忍着的、从喉咙里挤出来的、细细的哭声。她们的男人回来了,她们不用当寡妇了,她们的孩子不用当孤儿了——可她们哭。
因为她们知道,能回来,不容易。
因为她们知道,这四百七十三个男人,差点就回不来了。
因为她们知道,王后——王后能回来,更不容易。
阿姆从阿公身后走出来。
她脖子上那串骨珠还在,垂在胸前,在夕阳下泛着白森森的光。她走到她面前,站在她面前,望着她。
望着她那满身的吻痕。
望着她那个破了的嘴角。
望着她那双亮得像星星的眼睛。
阿姆抬起手。
那只满是皱纹的、干得像树皮的手。
伸过去。
轻轻碰了碰她的脸。
碰了碰那些吻痕。
碰了碰那个破了的嘴角。
然后阿姆开口。
“孩子,”那两个字从她那干裂的嘴唇里出来,哑得像风,“受苦了。”那三个字像三颗钉子。
钉在她心口上。
她没哭。
从河谷回来,她就没再哭过。
可此刻,阿姆那三个字说出来,她的眼睛湿了。
那湿盛在那儿,盛得满满的,盛得盛不下,终于掉下来。
一颗。
滴在阿姆的手上。
滴在那双干得像树皮的手上。
阿姆没躲。
只是用那只手,轻轻擦掉她脸上的泪。
擦得很轻。
轻得像怕弄疼她。
然后阿姆转身。
朝身后喊了一嗓子。
“来人——!给王后烧水——!熬肉汤——!拿最好的皮子——!”那些人动起来。
动得很快。
动得像早就等着这一刻。
我牵着她的手。
走进营地。
走进那片帐篷。
走进那顶最大的、属于王的帐篷。
那帐篷我走的时候什么样,现在还什么样。那张床还在,那些兽皮还在,那盏油灯还在——可一切都不一样了。
因为她回来了。
因为我抱着她回来了。
因为从今以后,这帐篷里,会有两个人。
———那天晚上。
她洗完澡,喝了肉汤,躺在那些兽皮上。
那些兽皮很软,很厚,是阿公让人新铺的。最好的狼皮,最好的熊皮,最好的狐皮——全铺在床上,铺成一张软得像云一样的床。
她躺在上面。
裹着一件新的皮袍。
那皮袍是阿姆送来的,白的,软得像水,领口和袖口镶着雪白的狐皮,比她身上原来那件还好。
她躺着。
望着我。
那眼睛在油灯下一闪一闪。
我坐在床边。
握着她的手。
那手暖了,软了,不像在河谷时那么凉了。
她开口。
“儿,”那一个字从她嘴里出来,轻得像风,“睡不着。”“为什么?”“怕。”她说,“怕一睁眼,你又不见了。”那七个字像七颗钉子。
钉在我心口上。
我弯下腰。
躺在她身边。
躺在那堆软得像云一样的兽皮上。
躺在她旁边。
侧过身。
望着她。
她侧过身。
望着我。
近得能看见她眼睛里的我。
近得能数清她睫毛上的水汽。
近得能感觉到她的呼吸。
那呼吸热热的,扑在我脸上,扑在我嘴上,扑在我心里。
我抬起手。
碰了碰她的脸。
碰了碰那些还在的吻痕。
碰了碰那个还没好的嘴角。
她闭上眼睛。
那睫毛颤着,像两只受惊的蝴蝶。
我开口。
“妈,”那一个字从嘴里出来,轻得像风,“我在。”那两个字让她睁开眼睛。
那眼睛里亮。
亮得像那盏油灯。
亮得像那年出租屋里的那盏灯。
她没说话。
只是把脸凑过来。
凑到我面前。
近得嘴唇碰着嘴唇。
那一下碰得很轻。
轻得像那年出租屋里第一次亲她的时候——那种轻。
可那一下碰得也很重。
重得像这辈子、下辈子、下下辈子的重量。
我们就那么亲着。
躺着。
在那堆软得像云一样的兽皮上。
在那盏昏黄的油灯下。
在那些吻痕旁边。
在那个破了的嘴角旁边。
在那一声一声的、从帐篷外面传来的、马蹄和风声里。
亲着。
一直亲着。
亲到她呼吸乱起来。
亲到她手抓住我的衣服。
亲到她整个人往我怀里钻。
然后她松开。
望着我。
那眼睛亮得像两颗星星。
“儿,”那一个字从她嘴里出来,轻得像风,“今晚——今晚你要我吗?”那七个字像七颗火星子。
落进我心里那堆已经烧起来的火里。
轰的一下。
整颗心都烧起来。
烧得我浑身发热。
烧得我什么都顾不上了。
我翻身。
压在她身上。
压在那具柔软的、温暖的、满身痕迹的身体上。
她望着我。
望着我。
那眼睛里全是光。
全是那一句——“要吗?”我低下头。
把嘴唇贴在她耳边。
那耳边还有吻痕——红的,紫的,青的——密密麻麻的,从耳根一直蔓延到脖子。
我开口。
“要。”那一个字从嘴里出来,轻得像风。
可重得像命。
她的身体抖了一下。
从那里抖起来。
抖到腰。
抖到胸。
抖到那颗朱砂痣都在轻轻颤动。
然后她的手抬起来。
抱住我的背。
抱得很紧。
紧得像要把我揉进她身体里。
紧得像这辈子、下辈子、下下辈子都不松开。
那盏油灯还亮着。
昏黄的,暖暖的,照在我们身上。
照在那堆兽皮上。
照在她脸上。
照在我脸上。
照在那一片吻痕抓痕牙印上。
照在那颗朱砂痣上。
照在那个破了的嘴角上。
照在那双亮得像星星的眼睛里。
那眼睛里亮。
亮得像那盏灯。
亮得像那年出租屋里的那盏灯。
亮得像这辈子、下辈子、下下辈子的光。
———第二天。
我醒来的时候,她还睡着。
躺在我怀里,脸贴在我胸口,手抓着我的衣服,抓得紧紧的,紧得像怕我跑掉。
那盏油灯早灭了。
可帐篷里有光——从兽皮的缝隙里透进来的,一丝一丝的,金色的,是早晨的阳光。
我低头看她。
看她那张睡着的脸。
那些吻痕还在,可没那么红了,淡了些,像一朵快要谢的花。那个破了的嘴角结痂了,暗红色的,嵌在那片微微张开的嘴唇上。她的睫毛很长,密密地盖着眼睛,盖着那双亮得像星星的眼睛。
她睡得很沉。
呼吸均匀得很。
那呼吸一下一下扑在我胸口,暖暖的,痒痒的。
我没动。
就那么躺着。
让她靠着。
让她抓着。
让她睡着。
外面开始有人声。
马蹄声,说话声,锅碗瓢盆的声音——是营地醒来了,是那些活着回来的人在开始新的一天。
有人走到帐篷外面。
停下。
“王——!”是栓子的声音。
我没动。
只是轻轻应了一声。
“嗯。”“王——阿公让您过去——有大事商量——!”大事?
什么大事?
我低头看她。
她还在睡着,没醒。
我轻轻把手从她手里抽出来。她抓得很紧,抽的时候她眉头皱了一下,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,可没醒,只是翻了个身,继续睡。
我坐起来。
穿上衣服。
走出帐篷。
外面阳光刺眼。
我眯了眯眼。
栓子站在帐篷外面,脸上带着笑——那种憋不住的笑。
“王——阿公在议事帐等您——!说是有大喜事——!”大喜事?
我没问。
只是跟着他往议事帐走。
路过营地中间那块空地的时候,我看见了——那四百七十三个跟我去的骑手,全站在那儿。他们站在阳光下,站在那片空地上,站在那些火把烧过的黑印子旁边。他们脸上全带着笑——那种从心里往外冒的笑。
他们身边,是那些从灰狼部抢来的东西。
三百多匹马。
几百张皮子。
几十袋粮食。
还有——还有女人。
三十几个女人。
年轻的,年老的,高的,矮的,胖的,瘦的——全站在那儿,全穿着灰狼部的衣服,全低着头,全不敢看人。
那是从灰狼部抢来的女人。
是灰狼部的女人。
可现在,她们是战利品。
是我们白狼部的战利品。
那些骑手站在她们旁边,有的在挑,有的在看,有的已经挑好了,正拉着那女人的手,往自己帐篷走。
我站着看了一会儿。
栓子在我旁边笑。
“王——!您说过——杀了赫连,每人分五头牛,两个婆娘——!牛还没分,婆娘先分上了——!”我没说话。
只是看着那些女人。
看着那些低着的头。
看着那些被拉着手、往帐篷走的背影。
她们愿意吗?
也许愿意。也许不愿意。可在草原上,这不重要。重要的是——她们是战利品。是打赢了的人应得的。
就像赫连想抢走她一样。
就像我杀了赫连,把她抢回来一样。
这就是草原。
这就是规矩。
我转身。
往议事帐走。
———议事帐里,人很多。
阿公坐在最中间,旁边是阿姆,是那几个部落里最老的老人,是那些跟我去了灰狼部的、有头有脸的人。
我进去的时候,所有人站起来。
“王——!”那一声喊得很齐。
我摆摆手。
坐下。
阿公望着我。
那浑浊的眼睛里,有什么东西在闪。
“王,”他开口,那声音哑得像石头在石头上磨,“灰狼部——乱了。”那五个字像五颗雷。
炸在议事帐里。
炸得所有人都静了。
我望着阿公。
“怎么乱了?”“赫连那七个儿子,”阿公说,“从昨天开始,就打起来了。老大说他是长子,该继承首领。老二说老大是废物,不配。老三说老二算什么东西——七个人,七个派,七个帐篷,全在抢那个位置。”他顿了顿。
“已经死了三个了。”死了三个?
才三天,就死了三个?
阿公点点头。
“老四,老五,老七。全是昨天晚上死的。老大杀的。”他那张满是皱纹的脸上,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——是笑?还是别的什么?
“老大杀的?”“对。老大说老四老五老七不服他,杀了。现在灰狼部里,还剩四个——老大,老二,老三,老六。那四个现在谁也不服谁,正召集自己的人,准备开打。”我听着。
听着听着,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开始转。
灰狼部乱了。
死了三个。
还剩四个。
那四个要打起来。
打起来,就会死人。
死人,就会更乱。
更乱,就会——“王,”阿公的声音把我拉回来,“这是个机会。”我望着他。
“什么机会?”“打下灰狼部的机会。”阿公一字一顿,“现在他们乱了,没首领,没人管,没人在意我们。我们可以——”他没说完。
可我知道他想说什么。
他想说,我们可以趁乱打过去。
可以杀了那四个。
可以吞并灰狼部。
可以把那五万帐、那两万能打仗的勇士,全变成我们的。
那念头像一颗火星子。
落进我心里那堆火里。
轰的一下。
烧起来。
烧得我眼睛发红。
烧得我浑身发热。
烧得我——站起来。
“召集人手。”我说。
那四个字从嘴里出来,很响。
响到整个议事帐都静了。
阿公望着我。
那浑浊的眼睛里,有什么东西亮起来。
“王——您决定——?”“决定。”我说,“趁他们乱,打过去。吞了灰狼部。”那八个字说出来,议事帐里炸了。
那些老人站起来,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站起来,全望着我,全张着嘴,全想说什么可又说不出来。
阿公也站起来。
拄着那根拐杖,站在我面前。
望着我。
望着我。
然后他开口。
“王,”那一个字从嘴里出来,颤颤的,“灰狼部——有五万帐。有两万能打仗的勇士。我们——”“我知道他们有多少人。”我打断他,“可那是平时。现在他们乱了,死了三个,剩四个在抢位置。他们顾不上我们。”我顿了顿。
“而且——”我望着阿公。
望着他那双浑浊的眼睛。
“而且,我们有她。”那三个字从嘴里出来,很轻。
可重得像山。
阿公愣了一下。
“她?”“神女。”我说,“灰狼部的人相信她是神女。赫连为什么没碰她?就因为她是神女,要把第一次留在神庙里。灰狼部的人信这个。”我望着阿公。
“如果我们带着她去——”阿公的眼睛亮了。
亮得像两盏灯。
“王——您是说——”“我说,”我一字一顿,“让她去告诉他们——长生天怒了。因为赫连抢了神女。所以赫连死了。所以灰狼部乱了。所以——”我顿了顿。
“所以,只有归顺白狼部,归顺神女的男人,才能活下去。”那几句话说出来,议事帐里静了。
死一般的静。
只有那些老人的呼吸声。
只有阿公那拐杖轻轻敲在地上的声音。
然后有人开口。
是阿姆。
“王,”她的声音很轻,“神女——她愿意吗?”那六个字像六颗钉子。
钉在我心口上。
她愿意吗?
我不知道。
我没问她。
从昨晚到现在,我只顾着抱她,亲她,要她——我没问她愿不愿意再做一次神女。愿不愿意再去灰狼部。愿不愿意站在那些人面前,说那些话。
我沉默了。
阿公望着我。
那浑浊的眼睛里,有什么东西在闪。
“王,”他说,“神女——她不只是你的女人。她是我们的神女。整个草原的神女。”他顿了顿。
“如果她愿意——如果她愿意帮这个忙——灰狼部,就是我们的了。”我站着。
站着。
站着。
脑子里全是一个画面——她站在灰狼部的人面前。
站在那些刚死了首领、正乱成一团的人面前。
站在那些相信她是神女的人面前。
她开口。
说那些话。
那些人跪下。
归顺。
灰狼部变成白狼部。
五万帐变成五万三千帐。
两万能打仗的勇士变成两万三千。
我和她——我转身。
走出议事帐。
走回我的帐篷。
掀开帐帘。
她醒了。
坐在床上,裹着那件白皮袍,望着我。那眼睛亮亮的,刚睡醒的那种亮,带着一点点迷糊。
“儿?”那一个字从她嘴里出来,软软的,“你去哪儿了?”我走过去。
坐在床边。
握着她的手。
望着她的眼睛。
那眼睛里有我。
有我一个人。
我开口。
“妈,”那一个字从嘴里出来,很轻,“有件事,要问你。”她愣了一下。
“什么事?”我望着她。
望着那双亮亮的眼睛。
然后我把阿公的话,把灰狼部的乱,把那个念头——全说了。
说完的时候,她沉默了很久。
很久。
久到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。
咚、咚、咚。
一下一下,砸得生疼。
然后她开口。
“我去。”那两个字从她嘴里出来,轻得像风。
可重得像山。
我望着她。
望着她那亮亮的眼睛。
“你——愿意?”她点头。
那一下点得很轻。
可点得很重。
“我愿意。”她说,“为了你——我什么都愿意。”那九个字像九颗心。
落进我心里。
落得稳稳的。
落得实实的。
落得这辈子、下辈子、下下辈子都不会再动。
我抱住她。
抱住那具柔软的、温暖的、满身痕迹的身体。
抱住那个从昨晚到现在一直在我怀里的女人。
抱住我妈。
抱住我的王后。
抱住我的命。
她在我怀里。
轻轻开口。
“儿,”那一个字从她嘴里出来,轻得像风,“什么时候去?”“今天。”我说。
她没说话。
只是把我抱得更紧了。
紧得像这辈子、下辈子、下下辈子都不松开。
———那天下午。
我们又出发了。
还是那四百七十三个骑手。还是那些马。还是那把刀。还是那片草原。
可这次不一样。
这次,我怀里抱着她。
这次,她是神女。
这次,我们要去的地方,不是杀赫连——是吞了整个灰狼部。
马蹄声又响了。
碎碎的,密密的,像一场下不完的雨。
她靠在我怀里。
望着那片灰蒙蒙的、永远也跑不到头的草原。
然后她开口。
“儿,”那一个字从她嘴里出来,轻得像风,“你说——他们会信吗?”“会。”我说。
“为什么?”“因为你是神女。”我说,“因为长生天站在你这边。”她沉默了一会儿。
然后她又开口。
“长生天——真的站在我们这边吗?”我望着她。
望着她那亮亮的眼睛。
“会。”我说,“因为你是我的女人。你的长生天,就是我的长生天。”她笑了。
那笑从那亮亮的眼睛里溢出来,溢得满脸都是,溢得那草原都在晃。
我们走着。
走着。
走向那片叫灰狼部的地方。
走向那片乱成一团的地方。
走向那片——属于我们的地方。
———三天后。
灰狼部营地。
夕阳西下,把那片密密麻麻的帐篷染成金色。
那四个赫连的儿子,还在打。
老大占着营地东边,老二占着西边,老三占着北边,老六占着南边。四个人,四片帐篷,四堆火,四拨人,谁也不服谁,谁也不让谁。白天打,晚上也打,打得头破血流,打得尸横遍野,打得那五万帐的人,死了快一万。
他们没注意到我们。
没注意到那四百七十三个骑手,已经悄悄摸到了营地外面。
没注意到我怀里抱着的那个女人。
没注意到——她站在营地门口。
站在那片夕阳里。
站在那四百七十三个骑手前面。
穿着那件白皮袍。
头发披着。
脸上那些吻痕还在——可那些吻痕,此刻不是耻辱,是证据。是赫连抢走她、赫连想碰她、赫连没敢碰她、赫连死了的证据。
她开口。
那声音很响。
响到整个营地都能听见。
“灰狼部的人——!”那六个字从她嘴里出来,像打雷,像山崩,像一万只狼同时嚎叫。
营地静了。
那些正在打架的人停下来。
那些正在流血的人停下来。
那些正在喊杀的人停下来。
全望着她。
全望着那个站在夕阳里、穿着白皮袍、满脸吻痕的女人。
她继续开口。
“我是神女——!”那五个字从她嘴里出来,更响了。
响到那些人的刀掉在地上。
响到那些人跪下去。
响到那四个赫连的儿子,从各自的帐篷里冲出来,站在各自的火堆旁边,望着她。
她望着他们。
望着那四个浑身是血、满脸杀气的年轻人。
然后她开口。
“赫连抢了我——长生天怒了——!”那十个字从她嘴里出来,像十道雷。
炸在那片营地上。
炸得那些人浑身发抖。
炸得那四个赫连的儿子,脸色全白了。
她往前走了一步。
就一步。
站在那片夕阳里。
站在那些跪着的人面前。
站在那四个脸色发白的年轻人面前。
然后她抬起手。
指着天。
“长生天说——只有归顺白狼部,归顺我的男人——才能活下去——!”那声音太响了。
响到那些人开始哭。
响到那些人开始磕头。
响到那四个赫连的儿子,互相看了一眼——然后跪下。
四个全跪下。
跪在她面前。
跪在那片夕阳里。
跪在那四百七十三个骑手面前。
跪在我面前。
我骑着马。
站在她身后。
望着那四个跪着的年轻人。
望着那五万帐的、正在跪下的、正在磕头的、正在哭喊的人。
然后我开口。
“从今天起——灰狼部,没了。”那八个字从嘴里出来,很响。
响到整个草原都能听见。
“从今天起——只有白狼部——!”那欢呼声响起来。
响得像打雷,像山崩,像一万只狼同时嚎叫。
她转过身。
望着我。
那眼睛亮得像星星。
亮得像那夕阳。
亮得像这一辈子的光。
———几天后。
白狼部营地。
我的帐篷外面,立着两根木桩。
木桩上,挂着两个东西。
两颗人头。
一颗是阿勒坦的——那个我刚来草原时、不服我当王、带头闹事、被我当众砍死的头人。他的头已经干得差不多了,皮贴着骨头,眼睛凹进去,嘴张着,露出那几颗黄牙。
一颗是赫连的——那个灰狼部的首领,那个抢走她的人,那个被我砍死在洞房花烛夜的人。他的头还新鲜些,眼睛还闭着,脖子上那个刀口还在,暗红色的,像一道永远合不上的嘴。
两颗人头。
挂在两根木桩上。
挂在帐篷门口。
挂在所有人进进出出都能看见的地方。
这是草原上的规矩。
杀了敌人,把头砍下来,挂起来——炫耀武功,震慑敌人。
阿勒坦和赫连,两个狼部首领,就这么挂着。
风吹过来,那两颗人头轻轻晃动,像在点头。
阿公站在我旁边。
望着那两颗人头。
那双浑浊的眼睛里,有什么东西在闪。
“王,”他的声音很哑,“三十年了——三十年了,从没人敢把灰狼部首领的头挂在自己帐篷外面。”我望着那两颗人头。
没说话。
阿公继续说。
“可您挂了。您不但挂了,还把灰狼部整个吞了。”他顿了顿,“现在——整个草原都知道,白狼部出了一个新王。一个敢杀赫连、敢吞灰狼部、敢把两颗狼头挂起来的新王。”我听着。
听着听着,忽然听见别的声音。
马蹄声。
很多马蹄声。
从远处传来,越来越近,越来越响。
我抬起头。
望向那边。
远处的地平线上,出现了一片黑压压的影子。
是马。
很多人骑着马。
朝我们这边来。
阿公的脸色变了。
“那是——”他没说完。
可我知道那是什么。
那是黑狼部的人。
草原上最大的部落。
比灰狼部还大。比白狼部大十倍。有十万帐,有五万能打仗的勇士。一直盘踞在草原最肥美的地方,一直没人敢惹。
他们来干什么?
那队人马越来越近。
近到能看清那些人的脸。
为首的是一个中年人,骑着一匹纯黑的马,穿着一身纯黑的皮袍,脸上有一道很长的疤,从眉骨一直划到嘴角——像铁牛,可比铁牛那道深多了,长多了,狰狞多了。
他勒住马。
停在营地门口。
停在离我们几十步远的地方。
他身后,那几百个骑手全停下来。
全望着我。
全望着帐篷外面那两颗人头。
那中年人望着那两颗人头,望了很久。
然后他转过头。
望着我。
那双眼睛很黑,很冷,像两口深不见底的井。
他开口。
“你就是那个杀了赫连的人?”那声音很沉,很哑,像石头在石头上磨。
我望着他。
望着那双黑得像井的眼睛。
然后我开口。
“是。”那一个字从嘴里出来,很响。
他沉默了一会儿。
然后他笑了。
那笑从那道疤上扯开,扯得那疤都在动,像一条活过来的蜈蚣。
“好。”他说,“好。”然后他勒转马头。
带着那几百个骑手,走了。
走得很快。
走得像来时一样突然。
只剩那马蹄声,碎碎的,密密的,渐渐远去。
我站在原地。
望着那片远去的黑影。
阿公站在我旁边。
他的声音发抖。
“王——黑狼部——他们怕了。”我望着那片黑影。
没说话。
可我知道。
阿公说得对。
他们怕了。
怕什么?
怕那两颗人头。
怕杀了赫连的人。
怕吞了灰狼部的人。
怕那个敢把两颗狼头挂起来的人。
可那怕里,也有别的什么。
那是——那是警惕。
那是戒备。
那是——他们会来。
总有一天,他们会来。
来试探我。
来试探白狼部。
来试探这个敢把两颗狼头挂起来的新王。
我转身。
走回帐篷。
她坐在里面。
坐在那堆兽皮上。
望着我。
那眼睛亮亮的。
“儿——?”那一个字从她嘴里出来,轻轻的,“刚才——谁来了?”我走过去。
坐在她身边。
握着她的手。
望着她的眼睛。
“黑狼部。”我说。
她愣了一下。
“黑狼部——他们来干什么?”我望着她。
望着那双亮亮的眼睛。
“来看。”我说,“来看那两颗人头。”她沉默了一会儿。
然后她开口。
“他们——怕了?”“怕了。”我说,“可也——”我顿了顿。
“也什么?”“也怕。”我说,“怕我们。”她望着我。
望着我。
然后她轻轻靠过来。
靠在我肩上。
那一下靠得很轻。
轻得像羽毛。
可那一下靠得很重。
重得像山。
她开口。
“儿,”那一个字从她嘴里出来,轻得像风,“不管谁来——我都陪着你。”那七个字像七颗心。
落进我心里。
落得稳稳的。
落得实实的。
落得这辈子、下辈子、下下辈子都不会再动。
我低下头。
把嘴唇印在她额头上。
印在那片还有吻痕的额头上。
印在那片属于我的额头上。
外面,那两颗人头还在晃。
风吹过来,晃得轻轻响。
远处,那片远去的黑影已经看不见了。
可我知道——他们还会回来。
总有一天,会回来。
可我不怕。
因为我有她。
因为她是我的女人。
因为她是我的神女。
因为她是我的命。
帐篷外面,那两颗狼头晃着。
帐篷里面,她在我怀里。
那盏油灯又亮起来。
昏黄的,暖暖的,照在我们身上。
照在那堆兽皮上。
照在她脸上。
照在我脸上。
照在那片吻痕上。
照在那颗朱砂痣上。
照在那双亮得像星星的眼睛里。
那眼睛里亮。
亮得像那盏灯。
亮得像那年出租屋里的那盏灯。
亮得像这辈子、下辈子、下下辈子的光。
那光里,有过去。
有现在。
有未来。
有那个十平米的出租屋。
有这片无边无际的草原。
有那两颗晃着的人头。
有那个远去的黑狼部。
有她。
有我。
有我们。
那天晚上,她在我怀里躺了很久。
那盏油灯已经添了两次油,昏黄的光晕在帐篷顶上晃着,晃得那些兽皮的影子也跟着动。她的手放在我胸口,手指轻轻划着那些干了的血痂——那是我杀赫连时溅上的,一直没洗掉,此刻在她指尖下,一片一片地往下掉。
“儿,”她开口,那声音软得像这帐篷里的光,“黑狼部——你真的不怕?”我握着她的手。
那只手很小,软软的,手指细长,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。在那边,这双手涂过各种颜色的指甲油,红的,粉的,紫的——可在这边,这双手什么也没涂,只有几道新添的细小的口子,是那天在河谷里洗皮袍时划破的。
“怕什么?”“怕他们打过来。”她说,“十万帐,五万能打仗的勇士。我们才五万三千帐,两万三千人。差一半呢。”我没说话。
只是望着帐篷顶。
那些兽皮的影子还在晃,晃得我眼睛有点花。
她等了一会儿,没等到我回答,就抬起头看我。
那眼睛在油灯下亮亮的,里面映着两团小小的火苗。
“儿?”我低下头。
望着她。
望着那双亮亮的眼睛。
“妈,”那一个字从嘴里出来,轻得像风,“你知道草原上为什么有这么多部落吗?”她愣了一下。
“为什么?”“因为没人能把他们合起来。”我说,“这个部族抢那个部族的女人,那个部族杀这个部族的人——打来打去,打了多少年,谁也灭不了谁。”我顿了顿。
“可如果有人能把他们都合起来——”她眼睛里的光闪了闪。
“那就没人能打了。”“对。”我说,“十万帐变成二十万帐,三十万帐——整个草原就是一个部落。那时候,谁还敢来抢?谁还敢来杀?”她沉默了一会儿。
然后她开口。
“你想——统一草原?”那五个字从她嘴里出来,轻轻的,可重得像石头。
我望着她。
望着她那双亮亮的眼睛。
“想。”我说。
那一个字从嘴里出来,很轻。
可也很重。
她没说话。
只是把我抱紧了。
抱得很紧。
紧得像要把我揉进她身体里。
过了很久。
久到那盏油灯又暗下去一点。
她开口。
“那就做。”她说,“你做什么,我都陪你。”那九个字像九颗心。
落进我心里。
落得稳稳的。
落得实实的。
———第二天。
议事帐里坐满了人。
阿公坐在最中间,旁边是阿姆,是那几个白狼部原来的长老。他们对面,坐着几个新来的面孔——是灰狼部的人,那几个赫连的儿子里活下来的,还有灰狼部原来的几个头人。
老大死了。
老二死了。
老三也死了。
就剩老六。
那个最小的,才十三岁,坐在那儿,缩着肩膀,眼睛都不敢抬。
他旁边站着一个女人——是他妈,赫连的一个女人,三十多岁,脸上有疤,眼神很凶。她一只手按在老六肩上,按得紧紧的,像怕他跑了。
那是灰狼部现在的当家人。
不是老六,是他妈。
我坐在最上首。
面前摆着一碗马奶子,酸酸的,腥腥的,我一口没喝。
阿公开口。
“王,”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哑,像石头在石头上磨,“黑狼部的事——您打算怎么办?”我望着他。
望着他那张满是皱纹的脸。
“打。”我说。
那一个字从嘴里出来,很响。
响到那几个灰狼部的人抬起头。
响到那个有疤的女人眼睛眯起来。
阿公没说话。
只是望着我。
等着。
我继续说。
“黑狼部现在怕我们。怕那两颗人头,怕杀了赫连的人,怕吞了灰狼部的人。”我顿了顿,“可那怕会变成别的。会变成恨,会变成杀意,会变成——趁我们还没站稳,打过来。”阿公点头。
“王说得对。”他说,“黑狼部那老狼王,我见过。狠着呢。当年他为了抢位置,杀了自己三个哥哥。这样的人,不会让一个比他狠的人活着。”我望着他。
“所以,趁他现在还没动手,我们先动手。”议事帐里静了一瞬。
然后有人开口。
是那个有疤的女人。
“王,”她的声音很粗,像男人,“你说打黑狼部——怎么打?他们有十万帐,我们才五万。”我望着她。
望着她那张带着疤的脸。
“你叫什么?”她愣了一下。
“我——我叫阿骨朵。”“阿骨朵,”我说,“你是灰狼部的人?”“是。”“你男人是赫连?”她的眼睛暗了一下。
“是。”“你恨我吗?”她没说话。
只是望着我。
那眼睛里有恨——我看得出来。可那恨里也有别的,有怕,有犹豫,有不知道该怎么办的那种茫然。
我继续问。
“你恨我杀了赫连?”她开口。
那声音更粗了。
“恨。”她说,“可那是草原上的规矩。他抢了你的女人,你杀了他,天经地义。”她顿了顿。
“而且——你留了我们母子一条命。没杀老六,没把我赏给手下。你——”她没说下去。
可我知道她想说什么。
她想说,你比我想的仁慈。
我没说话。
只是望着她。
望着她那双带着恨又带着别的什么的眼睛。
然后我开口。
“阿骨朵,”我说,“如果我打黑狼部,你愿意跟我去吗?”她愣住了。
“我?”“你。”我说,“你是灰狼部的人。你们灰狼部被黑狼部欺压了多少年——你心里清楚。”她沉默。
那沉默很长。
长到旁边那几个灰狼部的头人都开始交换眼神。
然后她开口。
“我跟你去。”她说。
那四个字从她嘴里出来,很响。
响到阿公的眼睛都亮了一下。
我站起来。
望着议事帐里所有人。
“那就这么定了。”我说,“今晚就动手。”———夜。
很黑。
没有月亮,只有星星,密密麻麻地铺在天上,像一把碎银子洒在黑绒布上。
我骑着马,走在队伍最前面。
身后不是四百七十三个骑手了。
是五千。
五千个骑手。
五千匹马。
五千把刀。
五千张弓。
那些灰狼部的人,那些刚归顺的人,那些被阿骨朵带着来的人——全在我身后,全骑着马,全握着刀,全望着我。
他们信我。
因为我是杀了赫连的人。
因为我是吞了灰狼部的人。
因为我是那个敢把两颗狼头挂起来的人。
现在,我要带他们去打黑狼部。
打那个草原上最大的部落。
打那个有十万帐、五万能打仗的勇士的部落。
马蹄声很轻。
我们走得很慢。
慢得像一群偷偷摸摸的狼。
前面,是黑狼部的营地。
那片营地太大了。
大得像一座城。
帐篷密密麻麻的,从这边一直延伸到那边,延伸到看不见的地方。火把也很多,一堆一堆的,像一片落在地上的星星。
我抬起手。
队伍停下来。
五千个人,五千匹马,全停下来。
全望着那片火光。
我望着那片火光。
望着那个最大的帐篷——那顶比所有帐篷都高出一截的、顶上插着一面黑狼旗的帐篷。
那是黑狼王的帐篷。
他在里面。
他老婆也在里面。
他孩子也在里面。
他全族人都在里面。
睡着。
等着。
等我们去杀。
我深吸一口气。
正要挥手——忽然,那边有动静。
马蹄声。
很多马蹄声。
从那片营地里传出来,越来越响,越来越近。
然后我看见——一群人骑着马,从营地里冲出来。
朝北边冲。
朝那片黑漆漆的山冲。
为首的是一个骑着纯黑马的人。
黑狼王。
他跑了。
———我们冲进营地的时候,里面已经乱了。
那些被惊醒的人从帐篷里冲出来,光着身子,拿着刀,嘴里喊着什么——可他们没头领,没指挥,没人在前面带着他们打。
因为头领跑了。
黑狼王跑了。
带着他那几百个部曲,跑了。
留下他的老婆孩子,留下他的族人,留下那十万帐的人,全扔在那儿。
我们没费多大力气。
那些黑狼部的人,看见我们冲进来,看见我们杀了几个人,就跪下了。
跪得很快。
跪得像早就等着这一刻。
我站在那顶最大的帐篷前面。
望着里面。
里面有人。
一个女人,三十多岁,穿着绸缎,头发披着,怀里抱着一个孩子——两岁左右,正在哭。她旁边站着几个大点的孩子,最大的也就十来岁,全缩在她身后,全望着我,全在发抖。
那是黑狼王的女人和孩子。
他扔下的。
我望着他们。
他们也望着我。
那女人开口。
她的声音发抖,可没哭。
“你——你是谁?”我望着她。
“杀赫连的人。”我说。
她的脸白了。
白得像纸。
可她没跪下。
只是把我抱得更紧了。
我转身。
走出帐篷。
外面,栓子跑过来。
“王——!黑狼王往北跑了——!往那片山上跑了——!要不要追——!”我望着北边。
那片山黑漆漆的,在星光下像一头蹲着的巨兽。
“追不上。”我说,“山太大,晚上看不清。等天亮。”栓子愣了一下。
“那——这些人——”我望着那些跪着的、缩着的、正在发抖的黑狼部的人。
“看着。”我说,“一个都不许跑。等天亮,等黑狼王回话。”———天亮。
太阳从东边升起来,照在那片山上。
照在那片黑狼王逃跑的山上。
也照在这片营地里。
十万帐的人,全跪着。
跪在空地上,跪在帐篷前面,跪在那顶最大的帐篷周围。男人,女人,老人,孩子——全跪着。全低着头。全在发抖。
我站在他们面前。
站在那顶最大的帐篷前面。
旁边站着阿骨朵,站着栓子,站着铁牛,站着阿燕。
还有她。
她站在我身边。
穿着那件白皮袍,披着头发,脸上那些吻痕已经淡得快看不见了,可那个破了的嘴角还有一点点痂,在阳光下泛着暗红色。
她望着那些跪着的人。
那些人也偷偷抬起头望她。
望他们的神女。
我抬起手。
人群静了。
我开口。
“黑狼王跑了。”那五个字从嘴里出来,很响,“扔下你们,扔下他的女人孩子,跑了。”静默。
死一般的静默。
然后有人开始哭。
一个女人,跪在人群前面,抱着一个孩子,哭起来。那哭声细细的,尖尖的,像刀子一样划破这早晨的空气。
接着是第二个。
第三个。
越来越多。
那哭声汇成一片,呜呜的,像风。
我没说话。
只是等着。
等他们哭够了。
等他们抬起头。
等他们望着我。
然后我开口。
“黑狼王不要你们了。”我说,“可我——”我顿了顿。
“我可以要你们。”那些眼睛。
那些刚哭过的、红红的、湿湿的眼睛,全望着我。
全望着我。
全望着我这个杀了赫连、吞了灰狼部、现在站在他们面前的人。
我继续说。
“只要你们归顺。只要你们认我是王。只要你们——把她当神女。”我指了指身边的她。
那些眼睛又望向她。
望向那个穿着白皮袍、披着头发、站在阳光下的女人。
她往前站了一步。
就一步。
站在那些跪着的人面前。
然后她开口。
那声音轻轻的,软软的,可每一个人都能听见。
“长生天让我来。”她说,“让我告诉你们——黑狼王不要你们了,可长生天还要你们。只要你们归顺,只要你们认他做王——”她指了指我。
“长生天就会保佑你们。保佑你们的牛羊,保佑你们的孩子,保佑你们的女人。”那声音像水。
流进那些人的耳朵里。
流进那些人的心里。
那些人开始动。
开始有人磕头。
开始有人喊——“神女——!”“神女——!”“神女——!”那喊声越来越大,越来越响,响得像打雷,像山崩,像十万个人同时喊那两个字。
我望着她。
她站在那喊声里,站在那阳光里,站在那些跪着的人面前。
她回过头。
望着我。
那眼睛亮亮的。
亮得像那阳光。
亮得像那年出租屋里她第一次对我说“妈爱你”的时候——那双眼睛里的光。
———中午。
我派出的信使回来了。
那是一个灰狼部的人,跑得很快,骑术很好。他骑着马,从那片山上下来,一直骑到我面前。
翻身下马。
跪下。
“王——!”“说。”“黑狼王——他——他回话了。”我望着他。
“说什么?”那信使抬起头。
脸上有汗,有土,还有一点犹豫。
“他说——他说——”“说什么?”“他说——”信使咽了口唾沫,“他说,如果王真的愿意招降他,不杀他——就应该派神女去。”那几句话说出来,周围静了。
静得能听见风的声音。
我站着。
望着那信使。
望着他那张满是汗的脸。
“派神女去?”“是。”信使的声音发抖,“他说——他信不过您。您杀了阿勒坦,杀了赫连——两颗人头还挂着呢。他说——除非神女亲自去,亲口说饶他不死,他才信。”我沉默。
很久。
久到那信使开始发抖。
久到旁边的人开始交换眼神。
然后有人开口。
是阿骨朵。
“王——不能派神女去!”她的声音很粗,很急,“黑狼王那老东西——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!神女要是去了——万一——”她没说下去。
可我知道她想说什么。
万一黑狼王把她扣下。
万一黑狼王把她——我不敢往下想。
我转过头。
望着她。
她站在我旁边,站在那阳光里,站在那些人的目光里。
她的脸上没什么表情。
只是望着我。
望着我。
那眼睛里有什么东西。
是平静。
是那种我熟悉的、从那个十平米出租屋里就开始有的平静——那种不管发生什么、她都会撑着的平静。
我开口。
“妈。”那一个字从嘴里出来,很轻。
只有她能听见。
她往前走了一步。
站在我面前。
站在那阳光里。
那阳光照在她脸上,照在她那件白皮袍上,照在她那双亮亮的眼睛上。
她抬起手。
碰了碰我的脸。
那只手暖暖的,软软的,带着阳光的温度。
“儿,”那一个字从她嘴里出来,也很轻,“让我去。”那四个字像四颗雷。
炸在我脑子里。
炸得我嗡嗡响。
“不行。”那两个字从嘴里出来,比我想的重。
她没说话。
只是望着我。
望着我。
那眼睛里有什么东西——是笑?是泪?是别的什么?
然后她开口。
“你信我吗?”那四个字像四颗钉子。
钉在我心口上。
我望着她。
望着她那双亮亮的眼睛。
“信。”那一个字从嘴里出来,很轻。
可很重。
她笑了。
那笑从那亮亮的眼睛里溢出来,溢得满脸都是,溢得那阳光都在晃。
“那就让我去。”她说,“你信我,我就不会有事。”我站着。
站着。
站着。
脑子里全是画面——她走进黑狼王的帐篷。
她站在那个老狼王面前。
她——我不敢想。
可我知道。
她说得对。
只有她去,黑狼王才会信。
只有她去,黑狼部才会真正归顺。
只有她去——我开口。
那声音哑得像石头在石头上磨。
“我陪你去。”她摇头。
“你不能去。”她说,“你去,他就不会出来了。他怕你,怕你杀他。只有我一个人去——他才会出来。”我望着她。
望着她那双亮亮的眼睛。
那眼睛里全是光。
全是那一句——“信我。”我闭上眼。
深吸一口气。
然后睁开。
“好。”我说。
那一个字从嘴里出来,像从心上剜下一块肉。
她笑了。
那笑比刚才更亮。
她踮起脚。
在我嘴唇上印了一下。
那一下很轻。
轻得像那年出租屋里第一次亲我的时候——那种轻。
然后她转身。
朝那匹马走去。
那匹马是她骑惯了的,一匹白色的马,很温顺,很听话。她翻身上马,坐在马上,回过头望我。
那眼睛亮亮的。
亮得像那阳光。
亮得像那年出租屋里她第一次对我说“妈爱你”的时候——那双眼睛里的光。
“等着我。”她说。
那三个字从她嘴里出来,轻得像风。
可重得像山。
然后她勒转马头。
马鞭扬起。
落下。
白马冲出去。
朝那片山冲去。
朝那个黑狼王藏身的地方冲去。
我站在原地。
望着她的背影。
望着那匹白马越跑越远。
望着那个白点越来越小。
最后消失在那片山的阴影里。
———山上。
黑狼王站在一块大石头后面。
他身后是那几百个部曲,全躲在石头后面,全握着刀,全紧张地望着山下。
山下,一匹白马正跑上来。
马上坐着一个女人。
穿着白皮袍,披着头发,脸白得像雪。
那是神女。
那是杀了赫连的那个男人的女人。
那是——他们等了半天的人。
黑狼王眯起眼睛。
那道疤在阳光下泛着暗红色,像一条活过来的蜈蚣。
他开口。
“就她一个?”旁边的人点头。
“就她一个。”黑狼王沉默了一会儿。
然后他笑了。
那笑从那道疤上扯开,扯得那疤都在动。
“好。”他说,“让她上来。”———白马跑到山腰。
那块大石头前面。
她勒住马。
翻身下马。
站在那块石头前面。
站在那几百个握着刀的人面前。
站在那个脸上有疤的老狼王面前。
阳光照在她身上。
照在她那件白皮袍上。
照在她那张没有表情的脸上。
她开口。
那声音很轻,很软,可那山里每一个人都能听见。
“黑狼王,”她说,“我来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