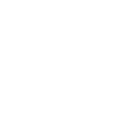12.妈妈跳脱衣舞诱惑黑狼王,我则绕到后边偷袭他
我站在原地,望着那匹白马消失在山影里。
手心里全是汗。
那汗是冷的,凉的,从掌心渗出来,顺着指缝往下淌,淌进那些还没长好的伤口里,蜇得生疼。
可我顾不上疼。
我只望着那片山。
望着那个她消失的方向。
脑子里全是画面——
她走进黑狼王的帐篷。
她站在那个老狼王面前。
那个老狼王脸上有道疤,长长的,从眉骨一直划到嘴角,笑起来像一条活过来的蜈蚣。
他会对她做什么?
他会像赫连那样——
我不敢往下想。
可那些画面自己会冒出来。
赫连的手按在她腰上、臀上、腿上的画面。她坐在赫连怀里的画面。她穿着那件红丝绸的画面。还有那个帐篷里,那堆污渍,那股气味,那些吻痕抓痕牙印——
那画面像刀。
一刀一刀割在我心上。
割得生疼。
疼得我浑身发抖。
可抖着抖着,我忽然不抖了。
因为我想明白了一件事——
我不能让她一个人去。
绝对不能。
赫连的事,差一点就出了事。如果不是赫连那狗东西信什么神女、要把第一次留在神庙里——她就——
我不能冒这个险。
不能再冒这个险。
我要去。
陪她去。
哪怕黑狼王认识我,哪怕他看见我就会跑,哪怕他会杀了我——我也要去。
可她说了,我不能去。
她说,只有她一个人去,黑狼王才会出来。
那怎么办?
我站在那儿,望着那片山,脑子里飞快地转。
忽然,一个念头冒出来——
仆人。
我可以扮成她的仆人。
化妆一下,谁能认出来?
我来草原才几天?那些部落的人,见过我的没几个。黑狼王远远看过我一眼,可那是骑在马上、穿着王袍的我。如果我换上破衣服,把脸涂黑,低着脑袋跟在她后面——
他认不出来。
肯定认不出来。
那念头一出来,就再也压不下去。
我转身。
往帐篷走。
走得很快。
快到栓子在后面喊——
“王——!您去哪儿——!”
我没理。
只是走。
走回那顶帐篷。
掀开帐帘。
———
帐篷里很暗。
那盏油灯没点,只有从兽皮缝隙里透进来的几缕光,一丝一丝的,像金色的线,落在那些兽皮上,落在那张床上,落在——
落在她身上。
她背对着我,站在床边上。
赤裸着。
可那赤裸和我刚才看见的不一样。
她正弯着腰,在穿什么东西。
那东西是黑色的。
薄薄的,透明的,从脚趾头一直往上卷,卷过脚踝,卷过小腿,卷过膝盖,卷过大腿——
丝袜。
黑丝。
那两个字像两颗雷,炸在我脑子里。
炸得我嗡嗡响。
她听见声音,回过头。
看见是我,她愣了一下,然后笑了。
那笑从那亮亮的眼睛里溢出来,溢得满脸都是。
“儿?”那一个字从她嘴里出来,轻轻的,“你怎么来了?”
我没说话。
只是望着她。
望着她那双正在穿丝袜的腿。
那腿我见过无数次。在那边,在那个十平米的出租屋里,在那张窄窄的床上,在那些热水蒸出来的雾气里——我见过无数次。
可我没见过这样的。
那丝袜太薄了。
薄得像一层雾,薄得像什么都没穿,可偏偏又裹得紧紧的,裹得那腿上的每一寸皮肤都泛着微微的光。那光从丝袜下面透出来,不是肉色的光,是那种被黑色衬出来的、更白更嫩的光。
她的腿本来就长。
本来就直。
本来就白。
可此刻被那黑丝裹着,那白更白了,那长更长了,那直更直了。从脚趾头开始,一路往上,脚踝细细的,小腿圆圆的,膝盖小小的,大腿——
那大腿。
那是我最喜欢的地方。
丰腴的,饱满的,软得像棉花,可又紧得像有弹性的棉花。此刻被那黑丝裹着,那丰腴更明显了,那饱满更突出了,那软——那软隔着丝袜都能感觉到。
她弯着腰,那大腿根部的肉被挤得微微隆起,从丝袜的边缘溢出来一点点——丝袜只到大腿根,再往上就没遮住了。
再往上是——
她穿着一条丁字裤。
也是黑色的。
细细的两根带子,一根在腰间,一根——
那根从后面绕过去,嵌在那两瓣臀肉中间。
那臀。
那是另一处我喜欢的地方。
浑圆的,挺翘的,像两座小山,又像两只倒扣着的碗。此刻那两瓣臀肉上什么也没遮,只有那根细细的黑带子嵌在中间,勒出一道浅浅的沟。那沟随着她的动作微微动着,一颤一颤的,像在说话。
再往上是腰。
细得不像话。
那腰我一只手就能握住。此刻光着,什么也没穿,只有那根丁字裤的黑带子系在腰间,勒出一点浅浅的红印。
再往上是背。
光滑的,白的,上面那些吻痕已经淡得快看不见了,只剩一点点红印子,像落花,像残雪,像马上要消失的什么东西。
再往上是——
她直起腰。
转过身。
面对着我。
那胸。
那是我最最喜欢的地方。
饱满的,挺立的,像两座山峰,又像两只熟透的瓜。此刻被一个黑色的文胸兜着——那文胸也是从那什么卡罗拉废墟掏出来的,薄薄的,透透的,蕾丝的,边缘镶着细细的花边。
那文胸太小了。
小得兜不住。
那两团乳肉被挤得从边缘溢出来,溢得满满的,鼓鼓的,上面全是细细的蕾丝印子。中间那道沟深得能夹住什么东西,在帐篷这昏暗的光里,那沟像一道山谷,又像一道邀请。
左乳上那颗朱砂痣还在。
暗红色的,嵌在那片被文胸边缘挤出来的乳肉上,在那黑色的蕾丝旁边,显得更红了,更艳了,更像一颗痣了。
那文胸的带子细细的,挂在肩上,勒出两道浅浅的印子。她的肩圆圆的,肉肉的,锁骨浅浅的,在那片白皮肤上画着两道弧线。
她站在那里。
穿着黑丝,穿着丁字裤,穿着那个性感文胸。
站在那几缕从兽皮缝隙里透进来的光里。
那光照在她身上,照在那黑丝上,黑丝反着光,亮亮的,像涂了一层油。照在那丁字裤上,那细细的黑带子反着光,亮亮的,像一根会发光的线。照在那个文胸上,那蕾丝花边反着光,亮亮的,像一片黑色的星星。
她整个人都在发光。
那光是黑的,也是白的,是亮的,也是暗的。
那光是——
“儿?”
她的声音把我拉回来。
我回过神来。
望着她。
望着她那亮亮的眼睛。
那眼睛里全是笑。那笑从眼睛里溢出来,溢得满脸都是,溢得那几缕光都在晃。
“你怎么来了?”她又问了一遍。
我张了张嘴。
想说话。
可那话卡在喉咙里,卡成一块石头。
因为我忽然想起我来干什么了。
我来是要告诉她——我要扮成仆人,陪她去。
可现在我望着她这样——
我忘了。
全忘了。
只记得看她。
看她穿着这身。
她见我不说话,笑得更厉害了。
那笑从嘴角溢出来,溢得那颗朱砂痣都在颤。
“好看吗?”她问。
那三个字从她嘴里出来,轻轻的,软软的,像那年出租屋里她第一次穿成这样问我——那种声音。
我点头。
那一下点得很重。
她笑了。
那笑里有什么东西——是得意?是欢喜?是那种“我就知道你喜欢”的娇?
她往前走了一步。
站在我面前。
站在那几缕光里。
近得能闻见她身上的气味。
那气味不是帐篷里的气味,不是草原上的气味——那是她自己的气味,带着晚香玉的残香,带着那黑丝、丁字裤、文胸上带着的、某种从那个世界带来的、久违了的、让我头晕的、香喷喷的气味。
那气味让我脑子里又嗡了一下。
我开口。
那声音哑得像石头在石头上磨。
“妈——你这是——”
她低头看了看自己。
看了看那黑丝裹着的腿,那丁字裤勒着的腰臀,那文胸兜着的胸。
然后她抬起头。
望着我。
那眼睛亮亮的。
“神女的装扮啊。”她说。
那五个字从她嘴里出来,轻轻的,理所当然的。
我愣了一下。
“神女的装扮?”
“嗯。”她点头,“去见黑狼王,总不能穿着那件皮袍去吧?那多没仪式感。”
仪式感。
那三个字从她嘴里出来,我脑子里转了好几圈才转明白。
“你是说——你要穿成这样——去见黑狼王?”
那话从嘴里出来,我自己都觉得酸。
酸得像喝了三大碗马奶子。
她望着我。
望着我。
然后她笑了。
那笑更厉害了,笑得那胸都在颤,笑得那颗朱砂痣一抖一抖的。
“你想什么呢?”她说,“外面还要穿衣服的。”
她转身。
从床上拿起一件东西。
那是一件皮袍。
可那不是普通的皮袍。
那是——
雪白色的。
白得像刚下的雪,白得像天上的云,白得像那年冬天出租屋窗外飘过的第一片雪花。
那皮袍很长,从领口一直垂到脚踝。领口和袖口镶着厚厚的狐皮,那狐毛也是雪白的,长长得垂下来,软得像水,像雾,像一碰就会化掉的东西。
她把那皮袍抖开。
披在身上。
那雪白的狐皮裹住她的身体,裹住那黑丝裹着的腿,裹住那丁字裤勒着的腰臀,裹住那文胸兜着的胸——可那裹不是真的裹。那皮袍是敞开的,只是在腰间系了一根带子,松松的,一拉就开。
那黑丝从皮袍下摆里露出来一点点。
就那么一点点。
小腿下面那一截。
黑色的,薄薄的,透明的,在那雪白的狐皮旁边,黑得更黑了,薄得更薄了,透明得更透明了。
那领口的狐毛堆在她脖子旁边,堆在她锁骨上面,堆在她那圆圆的肩头。那白毛衬着她的脸,衬得那脸更白了,那眼睛更亮了,那嘴角那个破了的痂更红了。
她站在那里。
穿着那雪白的狐皮大衣。
里面是黑丝,丁字裤,性感文胸。
站在那几缕光里。
站在我面前。
我望着她。
望着她。
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——
这是神女。
这是我的女人。
这是我妈。
这是要去见黑狼王的人。
那念头转着转着,忽然转出另一个念头——
我要陪她去。
扮成仆人。
我往前走了一步。
站在她面前。
站在那雪白的狐皮前面。
站在那黑丝露出的一截小腿前面。
我开口。
“妈,”那一个字从嘴里出来,轻轻的,“我也去。”
她愣了一下。
“你也去?可你说——”
“我扮成仆人。”我说,“化妆一下,黑狼王认不出来。”
她望着我。
望着我。
那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。
“你——你怕?”
那两个字像两颗钉子。
钉在我心口上。
我点头。
那一下点得很重。
“怕。”我说,“怕再出赫连那样的事。”
她沉默了一会儿。
然后她抬起手。
那只手从雪白的狐皮里伸出来,软软的,暖暖的,碰了碰我的脸。
碰了碰那些还没洗干净的、还带着赫连的血的脸。
“好。”她说。
那一个字从她嘴里出来,轻轻的。
可重得像山。
———
她帮我化妆。
用锅底的黑灰,用水和成糊糊,涂在我脸上,涂在我手上,涂在我能看见的所有皮肤上。那灰黑黑的,脏脏的,涂上去之后,我对着铜镜照了照——
认不出来。
连我自己都认不出来。
她又拿来一件破皮袍,灰扑扑的,全是补丁,领口袖口的毛都秃了,露出下面光光的皮子。那皮袍穿在身上,又脏又破又小,裹得我像个逃难的。
我站在她面前。
她望着我。
望着望着,她笑了。
那笑从那亮亮的眼睛里溢出来,溢得满脸都是。
“像。”她说,“真像个仆人。”
我望着她。
望着她穿着那雪白的狐皮大衣,站在那几缕光里。
“你呢?”我说,“你像神女。”
她低头看了看自己。
看了看那露出来的一截黑丝小腿。
然后她抬起头。
望着我。
那眼睛亮亮的。
“那当然。”她说,“我是神女嘛。”
那三个字从她嘴里出来,轻轻的,带着笑。
我走过去。
站在她面前。
近得能闻见她身上的气味——那晚香玉的残香,那黑丝丁字裤文胸带来的、久违了的香喷喷的气味,还有她自己的、让我头晕的气味。
我抬起手。
那黑黑的手。
帮她系那皮袍腰间的带子。
那带子是白的,和她身上那狐皮一样白。我的手黑黑的,在那白带子上显得更黑了。我系得很慢,很轻,系成一个活结,松松的,一拉就开。
她低头看着我系。
看着我的手。
看着那黑黑的手在那白白的带子上动着。
然后她开口。
“儿,”那一个字从她嘴里出来,轻轻的,“你真好。”
那三个字像三颗心。
落进我心里。
落得稳稳的。
落得实实的。
我系好带子。
抬起头。
望着她。
望着她那亮亮的眼睛。
“走吧。”我说。
她点头。
那一下点得很轻。
可点得很重。
———
我们走出帐篷。
外面阳光刺眼。
她走在前面。
穿着那雪白的狐皮大衣,踩着那双从卡罗拉废墟掏出来的、细细的高跟靴子——那靴子也是黑的,亮亮的,鞋跟又细又高,踩在地上咯噔咯噔响。
那靴子让她的腿显得更长。
那皮袍让她的腰显得更细。
那狐毛让她的脸显得更白。
她走在阳光下。
走在那些人的目光里。
那些人全望着她。
全望着这个穿着雪白狐皮大衣、踩着细细高跟鞋、走起路来咯噔咯噔响的女人。
全望着这个神女。
我走在她身后。
低着脑袋。
弯着腰。
穿着那件灰扑扑的破皮袍,脸上黑黑的,手上黑黑的,像个真正的仆人。
可我的眼睛没低。
我的眼睛一直望着她。
望着她那被黑丝裹着的小腿,从皮袍下摆里露出来,一截一截的,在阳光下反着光。
望着她那被皮袍裹着的腰臀,一扭一扭的,扭得那皮袍的下摆都在晃。
望着她那背影。
那属于我的背影。
那要去见黑狼王的背影。
栓子跑过来。
“王——!您——您怎么——”
他望着我,眼睛瞪得老大,嘴张着,说不出话来。
我看了他一眼。
那一眼让他闭上嘴。
他明白了。
他不问了。
只是望着她。
望着那个穿着雪白狐皮大衣、踩着细细高跟鞋、走起路来咯噔咯噔响的神女。
然后他开口。
“神女——马备好了。”
她点头。
那一下点得很轻。
她走到那匹白马旁边。
那匹马是她骑惯了的,很温顺,很听话。她抬起脚,那细细的高跟鞋踩进马镫里,那黑丝裹着的小腿在那阳光下亮了一下——
然后她翻身上马。
坐在马上。
那雪白的狐皮大衣从她身上滑落一点,露出更多黑丝裹着的腿。那腿夹着马腹,那黑丝在阳光下亮得像会发光。
她坐在马上。
回过头。
望着我。
那眼睛亮亮的。
“仆人,”她说,那声音轻轻的,可每一个人都能听见,“跟上。”
我低下头。
弯着腰。
走到一匹灰马旁边。
那马是栓子给我备的,灰扑扑的,又矮又丑,配我这身破皮袍正好。
我翻身上马。
那马走了一步。
我抬起头。
望着她。
她已经在前面了。
骑着那匹白马,穿着那雪白的狐皮大衣,踩着那细细的高跟靴子,露出那一截黑丝裹着的小腿。
她走在阳光下。
走在那些人的目光里。
走在那条通往山上的路。
我骑着那匹灰马,跟在她后面。
隔着十几步远。
低着脑袋。
弯着腰。
像个真正的仆人。
可我的眼睛一直望着她。
一直望着。
望着那雪白的背影。
望着那黑丝的一截。
山上。
那匹白马还拴在石头旁边。
她骑着马,我牵着马。
一前一后,往山上走。
山路很陡,全是碎石和枯草。我牵着马,一步一步往上走,眼睛一直盯着前面,盯着那些石头后面藏着的人影。
那些人影在动。
在盯着我们。
在等着我们。
终于,走到那块大石头前面。
石头后面,走出几个人。
拿着长矛。
穿着黑狼部的衣服。
为首的是一个脸上有疤的年轻人——比黑狼王那道疤浅多了,可也够吓人的。
他拦住我们。
“站住。”我和她停下来。
那年轻人望着她——望着那件雪白的狐皮大衣,望着那领口露出的、隐约可见的黑色文胸的边缘,望着那张脸,望着那个破了的嘴角。
他的眼睛直了。
直得像两根棍子。
她开口。
那声音轻轻的,软软的。
“我是神女。黑狼王让我来的。”那年轻人回过神来。
咽了口唾沫。
“神——神女——请——请进——”他的声音结结巴巴的,“可是——只能您一个人进——”他指了指我。
“这个——这个不能进。”我站着。
没动。
她转过头。
望了望我。
然后她转回去,望着那个年轻人。
那眼睛里的光变了。
变得冷。
变得硬。
变得像那天晚上在赫连帐篷外面、她走出帐篷、站在那四百多个跪着的人面前的时候——那种光。
她开口。
那声音还是轻轻的,软软的。
可那轻软里,有刀。
“这个男人,”她说,“是我的贴身男仆。他必须跟我进去。”那年轻人愣住了。
“可——可是——黑狼王说——”“黑狼王说什么?”她打断他,“黑狼王说让我来。我来了。可我没说一个人来。”那年轻人张了张嘴。
说不出话。
她继续说。
“他是我的男仆。从白狼部就一直跟着我。我洗澡他伺候,我换衣服他伺候,我睡觉他也在旁边守着。”她顿了顿,“我去哪儿,他就去哪儿。我活着,他就活着。我死了——”她没说完。
可那意思谁都懂。
那年轻人的脸白了。
白得像纸。
他回头望了望那些拿长矛的人。
那些人也在望他。
全在望他。
全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她又开口。
那声音更冷了。
“如果黑狼王不允许我带男仆进去——那就让他准备好。准备好和白狼部、灰狼部的联军开战。”那两句话像两颗雷。
炸在那年轻人耳边。
炸得他浑身一抖。
开战。
白狼部和灰狼部的联军。
那不就是——他猛地抬起头。
望着我。
望着我这个满脸黑灰、穿着破衣服的男人。
他的眼睛里有疑惑——这人是谁?为什么神女非要带他进去?
可那疑惑很快就变成了别的。
变成了怕。
变成了“万一得罪了神女、万一真的开战”的那种怕。
他往后退了一步。
“请——请进——”他的声音抖着,“神女——请进——您的男仆——也——也请进——”她没说话。
只是转过头。
望了我一眼。
那眼睛里有笑。
那笑从那冷冷的眼睛里溢出来,溢得那一瞬间的冷都化了。
然后她继续往前走。
我牵着马,跟在她身后。
走过那些拿长矛的人。
走过那块大石头。
走进那片藏着黑狼王的山腰。
身后,那些人还站着。
站着望着我们。
望着那个穿着雪白狐皮大衣的神女。
望着那个满脸黑灰、穿着破衣服的男人。
望着那两个一前一后走进山里的身影。
——山腰深处。
有一个山洞。
很大。
洞口站着更多的人。拿着刀,拿着弓,拿着长矛。全是黑狼王的部曲,全是跟着他从营地里跑出来的那几百个人。
他们望着我们。
望着那匹白马。
望着那个穿着雪白狐皮大衣的女人。
望着那个牵着马、满脸黑灰的男人。
那眼神里有惊艳,有疑惑,有警惕。
她没理他们。
只是往前走。
走到洞口。
停下。
洞口里面,有光。
火光。
还有一个人影。
那人影坐在最里面,坐在一块铺着兽皮的石头上。
脸上有一道很长的疤。
从眉骨一直划到嘴角。
黑狼王。
她站在洞口。
站在那火光能照到的地方。
然后她开口。
那声音轻轻的,软软的。
“黑狼王,”她说,“我来了。”山洞里静了一瞬。
然后那个人影动了一下。
站起来。
走出来。
走进火光里。
那张脸被火光照亮了——很老,很黑,满是皱纹。皱纹里嵌着尘土,嵌着血痂,嵌着这些年厮杀留下的痕迹。那道疤从眉骨开始,划过眼睛,划过脸颊,一直划到嘴角,把那张脸劈成两半。疤是暗红色的,在火光下一闪一闪,像一条活过来的蜈蚣。
他望着她。
望着这个穿着雪白狐皮大衣的女人。
那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动。
是惊艳。
是欲望。
是那种老狼看见猎物时的光。
“神女。”他开口,那声音沙哑得像石头在石头上磨,“你真的来了。”她点头。
那一下点得很轻。
“我来了。”她说,“来给你跳舞。”黑狼王的眼睛眯起来。
那道疤跟着动了一下。
“跳舞?”“祈福的舞。”她说,“你不是要吗?”黑狼王沉默了一会儿。
然后他笑了。
那笑从那道疤上扯开,扯得那疤都在动,扯得那张老脸更狰狞了。
“好。”他说,“好。”他往后退了一步。
坐回那块石头上。
然后他抬起手。
挥了挥。
山洞里那些部曲开始动。往后退,往洞口退,往洞外退。一个接一个,从我身边走过去,走出去。
最后,山洞里只剩下三个人。
他。
她。
还有我。
我站在洞口边,站在阴影里,低着脑袋,弯着腰,像个真正的仆人。我的手垂在身侧,握着一把藏在破皮袍下面的刀。那刀是栓子给我的,很短,很利,一刀下去能割断脖子。
黑狼王没看我。
他一眼都没看我。
他的眼睛全在她身上。
全在那个穿着雪白狐皮大衣的女人身上。
她站在火光里。
站在那块石头前面。
站在那个老狼王面前。
然后她动了。
她的手抬起来。
那手白白的,软软的,在那雪白的狐皮旁边,白得更白了。她的手碰到腰间那根带子——那根我亲手系上的、松松的、一拉就开的带子。
她轻轻一拉。
带子开了。
那雪白的狐皮大衣从她身上滑落。
很慢。
很慢很慢。
像一朵云从天上落下来。
那大衣从她肩上滑下去,滑过那圆圆的肩头,滑过那被黑色文胸裹着的胸,滑过那细细的腰,滑过那浑圆的臀,滑过那黑丝裹着的大腿——然后落在地上。
堆在她脚边。
堆成一堆雪白的狐皮。
她站在那堆雪白的狐皮上面。
站在那火光里。
站在那个老狼王面前。
穿着——黑丝。
丁字裤。
黑色文胸。
那黑丝从脚趾头开始,一路往上,裹着脚踝,裹着小腿,裹着膝盖,裹着大腿。薄薄的,透透的,在火光下反着光,亮亮的,像涂了一层油。那光从丝袜下面透出来,把她的腿衬得更白了,更长了,更直了。
那大腿根部的肉被丝袜的边缘勒出一点点痕迹,那痕迹浅浅的,红红的,在那片黑丝上面,在那片白肉上面,像两道细细的邀请。
再往上是丁字裤。
细细的两根黑带子,一根在腰间,勒出一道浅浅的红印。另一根从后面绕过去,嵌在那两瓣臀肉中间,勒出一道更深的沟。那两瓣臀肉浑圆的,挺翘的,在火光下反着光,白得晃眼。那根黑带子嵌在中间,随着她的呼吸微微动着,一颤一颤的。
再往上是腰。
细得不像话。那腰光着,什么也没穿,只有那丁字裤的黑带子系在腰间,勒出一点红印。那腰随着她的动作微微扭着,扭得那两瓣臀肉都在晃。
再往上是文胸。
黑色的,薄薄的,透透的,蕾丝的,边缘镶着细细的花边。那文胸太小了,小得兜不住那两团乳肉。那乳肉被挤得从边缘溢出来,溢得满满的,鼓鼓的,上面全是细细的蕾丝印子。中间那道沟深得能夹住什么东西,在火光里,那沟像一道山谷,又像一道邀请。
左乳上那颗朱砂痣还在。
暗红色的,嵌在那片被文胸边缘挤出来的乳肉上,在那黑色的蕾丝旁边,显得更红了,更艳了,更像一颗痣了。
她站在那里。
站在那堆雪白的狐皮上面。
站在那火光里。
站在那个老狼王面前。
黑狼王的呼吸变了。
变得粗了。
变得重了。
变得像一头真正的狼在喘气。
他的眼睛盯着她,盯着那黑丝裹着的腿,盯着那丁字裤勒着的腰臀,盯着那文胸兜着的胸。那眼睛里的光越来越亮,越来越烫,像两团火。
她没动。
只是站在那里。
让他看。
让他看够了。
然后她动了。
她的手抬起来。
手里多了一面手摇鼓——那鼓是从那堆狐皮里拿出来的,一直藏在里面。小小的,圆圆的,手柄上缠着皮条,鼓面上画着奇怪的图案。
她把鼓举起来。
轻轻一摇。
“咚——”那一声在山洞里响起来,闷闷的,沉沉的,像心跳。
她又摇了一下。
“咚——”然后是第三下。
“咚——”三声鼓响之后,她开始动。
那舞是从骨头里长出来的。
她的腰先动。那细细的腰开始扭,扭得很慢,很软,像一条蛇在游。那扭从腰传到臀,那浑圆的臀开始晃,晃得那两瓣肉都在颤,晃得那根嵌在中间的丁字裤带子都在动。那颤从臀传到腿,那黑丝裹着的腿开始动,动得那丝袜在火光下一闪一闪。
她往前走了一步。
踩着那细细的高跟靴子,咯噔一下。
那一步让她的胸晃了一下。
那两团被文胸兜着的乳肉颤了颤,颤得那颗朱砂痣都在抖。
黑狼王的喉咙里发出一个声音。
很低。
很沉。
像野兽的呜咽。
她没理他。
只是继续跳。
她的手抬起来,举着那面鼓,一边摇一边跳。那鼓声“咚咚”的,和她身体的节奏合在一起,一下一下的,像心跳,像喘息,像什么正在靠近的东西。
她的腰扭得更厉害了。
那扭从腰传到臀,那浑圆的臀开始画圈。画得很慢,很圆,一圈一圈的,画得那两瓣肉都在晃,画得那根丁字裤带子勒得更深了,画得那沟更明显了。
黑狼王的呼吸更重了。
他的身体往前倾,两只手抓着那块石头的边缘,抓得手指都白了。
她还在跳。
她抬起一条腿。
那黑丝裹着的腿。
她把那条腿抬起来,抬得很高,高得那大腿根部的丝袜边缘都露出来了,高得那丁字裤的侧面都露出来了。那条腿在空中伸着,伸得直直的,伸得那黑丝在火光下亮得刺眼。
然后她把那条腿放下来。
放在另一条腿前面。
交叉着。
那两条黑丝裹着的腿交叉在一起,互相蹭着,蹭得那丝袜发出细微的“沙沙”声。那蹭从脚踝开始,蹭过小腿,蹭过膝盖,蹭过大腿——蹭得那大腿根部的肉都在颤。
她一边蹭,一边往前走。
一步一步的。
踩着那细细的高跟鞋,咯噔,咯噔,咯噔。
朝黑狼王走去。
朝那块石头走去。
黑狼王的呼吸停了。
就那么停了。
他的眼睛瞪得老大,盯着她,盯着那两条交叉着走来的黑丝腿,盯着那扭动的腰,盯着那晃动的臀,盯着那颤动的胸。
她的脸离他越来越近。
近得他能看见她嘴角那个破了的痂。
近得他能闻见她身上的气味——晚香玉的残香,黑丝的味道,丁字裤的味道,文胸的味道,还有她自己的、让所有男人发疯的味道。
她在他面前停下来。
站在那块石头前面。
站在他两腿之间。
然后她低下头。
望着他。
望着那张满是皱纹的脸,望着那道像蜈蚣一样的疤,望着那双烧着火的眼睛。
她笑了。
那笑从嘴角溢出来,从那破了的痂旁边溢出来,溢得那张脸更亮了。
然后她抬起手。
那手白白的,软软的,举着那面鼓。
她把鼓举到他面前。
轻轻一摇。
“咚——”那一声响在他耳边,震得他浑身一抖。
她的另一只手抬起来。
碰到那文胸的边缘。
那黑色的蕾丝边缘。
她的手指伸进去,勾着那边缘,轻轻往下拉。
一点。
一点。
那文胸往下滑了一点点,露出更多乳肉。那乳肉白白的,嫩嫩的,在那黑色的蕾丝上面,显得更白了,更嫩了。那颗朱砂痣露出来更多,红红的,在那片白肉上,像一颗熟透的樱桃。
黑狼王的喉咙里又发出那个声音。
更响了。
更沉了。
更像野兽了。
她的手指继续往下拉。
那文胸又往下滑了一点点。
那乳肉露出来更多。
那乳沟更深了。
那乳晕的边缘露出来一点点——粉红色的,在那片白肉上,像两朵小小的花苞。
她停住了。
没再往下拉。
只是那样勾着文胸的边缘,让那乳肉露着一半,让那乳晕露着一点点,让那颗朱砂痣红红地在那儿晃。
然后她又动了。
她的另一只手放下来。
放在那条交叉着的腿上。
放在那黑丝裹着的大腿上。
她的手从那大腿上开始摸。
很慢。
很轻。
从那大腿根部开始,往下摸,摸过丝袜裹着的肉,摸过那薄薄的、透透的、滑滑的黑丝。那手摸得很慢,很慢很慢,慢得每一寸皮肤都能感觉到那手的温度。
黑狼王的眼珠子跟着那只手动。
从大腿根部,一路往下,往下,往下——摸过膝盖,摸过小腿,摸过脚踝,一直摸到那只穿着细细高跟鞋的脚。
然后她把那只脚抬起来。
抬起来。
抬起来。
抬到他面前。
那黑丝裹着的脚。
那细细的高跟鞋。
那脚就在他脸前面,近得他能闻见那高跟鞋上的皮革味,能闻见那黑丝下面的、她皮肤的味道。
她动了动脚趾头。
那黑丝裹着的脚趾头动了动,一动一动的,在那细细的鞋尖里面,像在说话。
黑狼王的呼吸彻底乱了。
乱得像一头被关了一万年的野兽,终于看见了门。
他的手抬起来。
朝那只脚伸去。
可她的手比他更快。
那只勾着文胸边缘的手放下来。
一把抓住他的手腕。
他愣住了。
抬起头。
望着她。
她望着他。
那眼睛亮亮的。
那亮里有光。
那光是——“别急。”她说,那声音轻轻的,软软的,“舞还没跳完。”她把那只脚收回来。
放回地上。
然后她转过身。
背对着他。
背对着那个坐在石头上的老狼王。
那背光光的,白白的,上面那些吻痕已经淡得快看不见了。那腰细细的,那臀浑圆的,那两瓣臀肉中间嵌着一根细细的黑带子,勒出一道深深的沟。
她把那臀对着他。
然后她开始扭。
那扭是从腰开始的。那细细的腰扭着,扭得那浑圆的臀开始晃,晃得那两瓣肉都在颤,颤得那根黑带子都在动。那晃越来越厉害,越来越厉害,晃得那臀肉像两团会动的云,晃得那沟一会儿深一会儿浅,晃得那丁字裤的带子一会儿勒紧一会儿松开。
黑狼王的呼吸像拉风箱。
呼哧,呼哧,呼哧。
他的手又抬起来。
朝那晃动的臀伸去。
可她又躲开了。
她往前走了一步。
离开他的手。
然后她弯下腰。
那腰弯下去,弯得那浑圆的臀翘得更高了,高得那丁字裤勒得更深了,高得那两瓣臀肉中间那道沟更明显了。那沟深深的,黑黑的,嵌着那根细细的黑带子,在火光下一闪一闪。
她弯着腰。
回过头。
望着他。
那眼睛从下面往上看,亮亮的,带着笑。
那笑在说——来啊。
来追我啊。
黑狼王再也忍不住了。
他猛地站起来。
朝她扑过去。
那动作快得像一头真正的狼。
她发出一声尖叫——不是怕。
是装出来的怕。
那尖叫让他的血更热了。
他的手抓住她的手腕。
他的脸埋进她的胸口。
埋进那被文胸兜着的、半露着的、白白的、嫩嫩的、软软的乳肉里。
他的嘴张开。
咬住那乳肉。
咬住那颗朱砂痣。
开始吮吸。
像婴儿。
像野兽。
像一头饿了一万年的狼。
她的身体僵了一下。
然后软下来。
软在他怀里。
她的手抬起来。
抱住他的头。
抱着那个埋在她胸口的、满是皱纹的、带着疤的头。
她的手指插进他的头发里。
轻轻地抚着。
像在安抚一头野兽。
可她的眼睛没在安抚。
她的眼睛在看我。
从那个抱着她的男人肩上看过来。
看着我。
那眼睛亮亮的。
那亮里有话——动手。
我的手动了。
那藏在破皮袍下面的刀拔出来。
很短。
很利。
我往前走了一步。
两步。
三步。
走到他身后。
走到那个正埋在我妈胸口吮吸的老狼王身后。
他的头还在动。
他的嘴还在吮。
他的手已经松开她的手腕,抱住她的腰,抱住那被黑丝裹着的腰,把她往自己身上按。
他完全没注意到我。
完全没注意到这个站在他身后的、满脸黑灰的、穿着破衣服的“仆人”。
我举起刀。
对准他的脖子。
那脖子很老,很多皱纹,那皱纹里嵌着尘土,嵌着血痂。那道疤从脸颊划下来,一直划到脖子上,在脖子侧面留下一道淡淡的痕迹。
我把刀对准那道痕迹。
然后——砍下去。
“噗——”那声音闷闷的,像砍在一块生肉上。
他的身体猛地一抖。
他的嘴从她胸口离开。
发出一声尖叫——“啊——!”那尖叫在山洞里炸开,炸得火光都在晃。
可他的手没松。
还抱着她的腰。
还把她往自己身上按。
我又是一刀。
砍在同一处。
“噗——”更深的。
更狠的。
这一次,我感觉到刀砍到了什么硬的东西——骨头。那骨头被我砍断了,发出“咔嚓”一声,很脆,很响,像折断一根枯枝。
血喷出来。
热热的,腥腥的,喷在我脸上,喷在我手上,喷在我那件破皮袍上。那血是暗红色的,在火光下黑黑的,像墨。
他的身体开始软。
他的手开始松。
他的头开始往下垂。
可还没完全垂下去。
我抓住他的头发。
那头发灰白的,粗粗的,硬硬的,像狼的鬃毛。
我用力一拉。
他的脖子露出来。
那脖子已经被我砍开一个大口子,血从那口子里往外涌,涌得那脖子上的肉都翻出来了,白白的,红红的,像一堆烂肉。那骨头断了一半,露出白森森的茬子,在那血里面,像一堆碎骨头。
我又是一刀。
砍在那断了一半的骨头上。
“咔嚓——”全断了。
他的头和身体分开了。
那脑袋被我抓在手里,沉沉的,热热的,还在往外滴血。那眼睛还睁着,瞪得老大,望着我,望着这个满脸黑灰的男人。那眼睛里有什么东西——是不信,是惊骇,是“你怎么敢”的那种光。
可那光很快就暗了。
灭了。
死了。
我把那脑袋拎起来。
转过身。
望着她。
她站在那儿。
站在那堆雪白的狐皮上面。
站在那火光里。
身上全是血。
那血喷在她胸口,喷在那被文胸兜着的乳肉上,喷在那颗朱砂痣上,喷在那黑丝裹着的腿上,喷在那丁字裤勒着的腰臀上。那血在她身上往下淌,淌过那乳沟,淌过那细细的腰,淌过那浑圆的臀,淌过那黑丝裹着的大腿——在那黑丝上面,那血是黑色的,亮亮的,像一层黑色的油。
她站在那里。
望着我。
望着我手里那个还在滴血的脑袋。
然后她笑了。
那笑从那亮亮的眼睛里溢出来,溢得满脸都是,溢得那脸上的血都在动。
她伸出手。
那手白白的,软软的,上面也沾着血。
她接过那个脑袋。
两只手捧着。
捧着那个曾经埋在她胸口吮吸的脑袋。
捧在她面前。
捧在她那沾着血的胸口前面。
那脑袋还在滴血。
滴在她胸上。
滴在那颗朱砂痣上。
滴在那黑丝裹着的腿上。
我望着她。
望着她捧着那个脑袋。
望着她站在那堆雪白的狐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