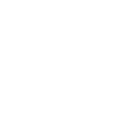21.玄凝冰将军的邀请
接下来的几天,我像是换了一个人。
第一天,安西来的那个游牧部落的勇士,身高九尺,膀大腰圆,手里提着一对铁锤,往我面前一站,像一座铁塔。他望着我,那眼睛里全是轻蔑,嘴里嘟囔着他们部落的话,旁边的通译说,他说“这小个子,一锤就砸扁了”。
我没说话。
他出手了。那对铁锤抡起来,带着呼呼的风声,往我头上砸下来。
我往旁边一闪,那锤砸在地上,“轰”的一声,砸出一个大坑。
周围的人都倒吸一口凉气。
我没等他把锤提起来,就动了。
柔道里头有个招,叫“大外刈”。趁着对手重心不稳的时候,用腿扫他的支撑腿,顺势把他撂倒。
我那一扫,正扫在他脚踝上。他那铁塔似的身子晃了晃,往旁边倒下去,轰隆一声,砸在地上,把那些围观的兵吓得往后退了好几步。
他躺在地上,那眼睛瞪得大大的,望着天,像是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。
我站在他旁边,伸手。
“起来吧。”
他愣了愣,抓住我的手,站起来。他望着我,那眼睛里的轻蔑没了,换了一种东西——是那种“我服了”的光。
他叽里咕噜说了几句,通译说,他说“你这是什么妖法?”
我没回答,只是笑了笑。
第二天,匈人游牧部落的勇士来了。
那家伙瘦得像根竹竿,可那胳膊上的肌肉一条一条的,像缠着绳子。他使的是一把弯刀,那刀在他手里转来转去,像活的一般。
他比我灵活,比我快,那弯刀舞得密不透风,我连近身的机会都没有。
可我有柔道。
柔道里头,最不怕的就是这种快刀。因为他快,所以他重心不稳。因为他转来转去,所以他总有破绽。
我等了半柱香的功夫,终于等到他一个踉跄。
就那一瞬间,我贴上去,一个“背负投”,把他从我肩上摔了过去。
他在空中翻了个身,落在地上,又滚了两滚,趴在那儿,半天没动。
那弯刀飞出老远,插在地上,刀柄还在晃。
周围的士兵们,静了那么一瞬,然后爆出一阵欢呼。
第三天,陇西军左营的比武冠军来了。
那是个使枪的高手,枪法比我第一回打败的那个右营的厉害得多。他那枪舞起来,像一条龙,上下翻飞,左右盘旋,我根本近不了身。
我被逼得连连后退,退到校场边上,再退就要出界了。
他得意起来,那枪更快了。
可我知道,这种得意的时候,就是他最疏忽的时候。
他刺过来一枪,我假装躲不过去,身子往后一仰。他果然上当,往前迈了一大步,想要一枪结果我。
就这一步。
我身子一扭,从他枪下钻过去,贴到他身边,一个“体落”,把他撂倒在地。
他那枪脱手,飞出去老远。他躺在地上,望着我,那眼睛里全是不信。
“你——你怎么——”
我没说话,只是伸手拉他起来。
他起来以后,望着我,那眼神复杂得很。
“你这是什么路子?”他问,“我从没见过这种打法。”
我想了想。
“草原上的打法。”我说,“跟熊学的。”
他愣了一下,然后笑了。
“跟熊学的?那你学得不错。”
第四天,第五天,第六天……
每天都有人上来挑战。西宁各营的,附近州府的,还有那些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游牧部落的勇士。有的使刀,有的使枪,有的使锤,有的使鞭。有的高大,有的矮小,有的快,有的狠。
可不管是谁,不管使什么,最后都躺在地上了。
柔道这东西,他们没见过。
那些摔法,那些反关节技,那些利用对手重心和力道的技巧——在他们看来,就是妖法,就是邪术,就是那种“不知道怎么就被撂倒了”的怪东西。
到了第七天,来的人越来越少。
不是没人想挑战,是那些有名的勇士,都被我摔怕了。那些没名的,更不敢上来。
我站在校场中央,望着周围那些人,望着那些复杂的眼神——有敬,有畏,有好奇,有不解。
远处,那面玄字旗还在风里飘。
那个骑着白马的人,每天都会来看。有时候站在那队银甲兵前面,有时候坐在搭建的高台上,有时候就那么骑着马,在校场边上远远地望着。
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。
那目光落在我身上,有一种东西——是打量,是探究,是那种“这人有点意思”的光。
第八天上午,玄凝冰的亲卫营来人了。
那是她的贴身护卫,一共五个,都是银甲银枪,骑着高头大马。他们从校场那头走过来,马蹄声齐整整的,踏在地上,像一阵闷雷。
为首的翻身下马,走到我面前。
他比我高出半个头,那身子壮得像头牛,那脸黑黑的,那眼睛亮亮的,那眼神里有一种东西——是那种“让我来试试你”的光。
“我叫铁雄。”他说,“玄将军的亲卫营副统领。听说你打败了这西宁城所有的高手,特来领教。”
我望着他。
“好。”
他使的是刀,一把厚背大刀,比寻常的刀重得多。他提在手里,像提着一根柴火,轻轻松松的。
我们交手了。
他确实厉害。比前几天的那些人都厉害。他那刀法大开大阖,力道沉猛,每一刀都有开山裂石之势。我被逼得连连后退,好几次差点被他劈中。
可柔道的长处,就是借力打力。
他越是用力,我越能找到破绽。
三十招之后,我瞅准他一个破绽,贴身上去,一个“大腰”,把他从我肩上摔了过去。
他在地上滚了两滚,爬起来,那脸上带着惊。
“再来!”
我们又打。
这回他学聪明了,不再猛冲猛打,而是稳扎稳打,一步一步地逼我。
打了五十几招,我又找到一个机会,把他撂倒了。
他又爬起来。
“再来!”
打了三场,他倒了三回。
第四回爬起来的时候,他望着我,那眼神里已经没有那种“试试你”的光了,换了一种东西——是那种“我服了”的敬。
“你厉害。”他说,“我打不过你。”
他收刀入鞘,冲我抱了抱拳,转身要走。
“等等。”我叫住他。
他回过头。
“你们一共五个人,”我说,“一起上吧。”
他愣了一下,那眼睛瞪得大大的。
“一起上?”
我点点头。
他望着我,那眼神里有一种东西——是那种“你是不是疯了”的怀疑。
可他还是回头,朝那四个人招了招手。
那四个人下了马,走过来,站在他身后。
五个人,五把刀,把我围在中间。
周围那些看热闹的人,一下子安静了。
静得出奇。
我站在那五个人中间,深深地吸了口气。
然后我开口。
“来吧。”
他们动了。
五把刀从五个方向劈过来,那刀光织成一张网,往我头上罩下来。
我没躲。
我往前冲。
冲向他们中最弱的那一个。
他没想到我会冲得这么快,那刀还没落下来,我已经到了他面前。我抓住他的手腕,一拧,那刀脱手。我顺势一推,把他撞向旁边的另一个人。
两个人撞在一起,滚成一团。
剩下的三个人愣了一下。
就这一愣的功夫,我又动了。
柔道里有一种招,叫“乱取”,就是一个人对多个人的时候,利用对手的混乱,一个一个地解决。
我就是这么干的。
先放倒一个。
再放倒一个。
再放倒一个。
剩下的两个慌了,那刀舞得乱了章法,被我瞅准破绽,一个一个撂倒。
等最后一个人躺在地上的时候,周围那些看热闹的人,静了那么一瞬。
然后那欢呼声像炸开了一样,轰地响起来。
“好!”
“厉害!”
“这他娘的是什么打法!”
我站在那五个人中间,喘着气,浑身的汗像水一样往下淌。
那五个人从地上爬起来,互相看看,又看看我,那眼神里全是一种东西——是那种“我们是服了”的光。
铁雄走到我面前,冲我抱了抱拳,深深地弯下腰。
“佩服。”
我回了个礼。
就在这时,人群突然安静了。
那安静像水一样,从校场那头漫过来,漫过那些欢呼的人,漫过那些躺在地上的亲卫,漫到我面前。
我抬起头。
人群自动让开一条路。
路的尽头,一个身影正往这边走来。
那是一个女人。
她穿着银色的甲,那甲片在阳光下亮得晃眼,一片一片的,把她那高挑丰腴的身子裹得严严实实。可那甲再严实,也遮不住她那惊心动魄的身段——肩宽背厚,却腰肢纤细;胸前隆起的甲片高高撑起,绷出两道饱满浑圆的弧线,随着步伐微微颤动,像是藏不住的两座小山;再往下,那腰身在甲裙的束裹下收得极紧,不盈一握;腰下却是骤然放开的浑圆弧线,那臀在甲裙下面鼓鼓的,翘翘的,把银色的甲裙撑得满满的,随着她迈步,一下一下的,像熟透的蜜桃在风里轻晃。她每走一步,那腰肢就轻轻一扭,那臀就微微一动,走得稳稳的,又带着一种说不出的风情。
她比我想象的还高。
我站起来,足有一米八。可她站在我面前,我竟要微微仰着脸,才能看见她的眼睛。
一米八五往上。那双腿笔直修长,裹在银色腿甲里,从腰胯一直延伸到靴口,像两根挺拔的玉柱,稳稳地扎在地上。
她站在那儿,望着我。那脸离我只有几步远,我能清清楚楚地看见她。
那脸不是十七八岁小姑娘的青涩。她看着三十五六岁年纪,可那三十五六岁在她脸上,不是老,是另外一种东西——是那种“经过事”的沉,是那种“见过血”的稳。那皮肤不是那种白嫩的,是带着淡淡麦色的,被风吹过,被日晒过,可那麦色下面,还是能看出底子里的白腻。
那眉眼生得极好。眉毛弯弯的,不是描出来的那种弯,是天生就那样弯,像两道细细的墨痕。眼睛大大的,眼珠子黑黑的,亮亮的,像两潭深水,却又藏着刀锋。那眼神落在我身上,有一种东西——是打量,是探究,还有一种我说不清的、让人心里一动的光。
那鼻子高高的,挺挺的。那嘴唇不厚不薄,抿着,嘴角微微往上翘,像是在笑,又像是没在笑。那下巴有点尖,可那尖里有刚,是那种“我说了算”的刚。
她站着,就那么站着。那身子在那银甲下面,是那种常年习武才有的身板——该鼓的地方鼓得高高的,该收的地方收得紧紧的,该翘的地方翘得圆圆的。胸前那两座小山随着呼吸微微起伏,腰肢纤细得像是能一手握住,那臀在身后撑出一道惊心动魄的弧线,把甲裙绷得一丝褶皱都没有。
她浑身上下,透着一种东西——是力,是美,是那种只有真正打过仗、杀过人才有的气。那气混着她这熟透了的身子,像一坛埋了多年的酒,光是站在那儿,就让人心里发醉。
她望着我。
我也望着她。
我们就这样望着,望了那么几息。
然后她开口了。
那声音从她嘴里出来,不是那种娇娇柔柔的女人的声音,也不是那种粗粗哑哑的男人的声音。那声音刚刚好,不高不低,不粗不细,可那不高不低里有沉,有不粗不细里有威。
“你叫什么?”
我望着她。
“韩天。”
她点点头。
“韩天。”她重复了一遍,那两个字从她嘴里出来,像两颗小石子落在水里,“你是哪儿人?看着不像安西这边的,倒有些像江南的公子。”
我没说话。
周德胜从旁边跑过来,跑到她面前,抱了抱拳。
“玄将军,”他说,那声音有点紧张,“这位韩兄弟,是江南人士,苏州府吴县的。当年跟着他爹去波斯做生意,迷了路,被蛮人掠了去。如今机缘巧合,已经是狼部镇守使了。”
玄凝冰转过头,望着周德胜。
“狼部镇守使?”
“是。”周德胜说,“朝廷册封的。驻藏大臣衙门出的文书。”
她点点头,又转过头来望着我。
那眼神里,多了一点东西——是那种“有点意思”的光。
“狼部,”她说,“在哪儿?”
“西边。”我说,“翻过几座山,靠近金沙江的地方。”
“多少人?”
“六万多。”
她点点头。
“六万多。”她说,“那不小了。”
她顿了顿,又望着我。
“听说你在草原上亲手杀了三个狼部的头人?”
我点点头。
“是。”
她没说话,就那么望着我。那眼神在我脸上转着,像在找什么。
然后她开口。
“为什么杀他们?”
我想了想。
“因为他们不服我。因为他们还想按老规矩办事——抢,杀,抢了再杀。因为他们挡着狼部的路,不让狼部的人过好日子。”
她听着,那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动。
我接着说:“我杀了他们,把他们的头砍下来,挂在杆子上,让所有狼部的人都看看——从今往后,狼部的规矩变了。不许抢,不许随便杀人,要跟汉人做买卖,要学着种地,要让孩子念书,要按朝廷的法子过日子。”
她没说话,就那么望着我。
那眼神,我看不懂。
周德胜在旁边,又往前凑了凑。
“玄将军,”他说,那声音压得很低,低得只有我们几个能听见,“昨儿个那个——那个怀表——就是这位韩兄弟送的。”
玄凝冰的眼睛动了一下。
只是一下。
很快。
可我看见了。
她望着我,那眼神里,有什么东西变了。
变得更深了。
更亮了。
更像是在看一个——一个不一样的人。
她开口。
那声音还是那样,不高不低,不粗不细。可那不高不低里,多了一点东西——是那种“我知道了”的沉。
“韩天,”她说,“你的表,我收下了。”
我点点头。
“应该的。”
她望着我,那嘴角动了动,像是在笑。
“你这个人,”她说,“有点意思。”
我没说话。
她转过身,朝那队银甲兵走去。
走了几步,又停下。
回过头,望着我。
“明天,”她说,“你来我帐中。我有话问你。”
我站在那儿,望着她的背影,望着那银色的甲在阳光下闪,望着那高高挑挑的身子走远——那走动时腰肢轻扭、臀波微动的样子,像一幅画。
心里那团东西,跳得厉害。
周德胜在旁边,轻轻地拍了我一下。
“韩兄弟,”他说,那声音里带着笑,“你成了。”
我没说话。
只是望着那越来越远的背影,望着那面在风里飘的玄字旗。
明天。
她帐中。
我有话问你。
我站在那儿,望着玄凝冰的背影,望着她走出几步,又停下,回过头来。
那目光落在我身上,有一种东西——是等,是那种“你怎么还不跟上”的等。
可我没动。
我望着她,开口。
“将军。”
她站住了。
“比武场上,”我说,“还是要分个输赢的。”
她的眼睛动了一下。
“将军要和我说话,那是将军的恩典。可在这之前,咱们得先把这比试的事了了。”
她转过身来,望着我。那嘴角微微动了动,像是在笑,又像是没在笑。
“你的意思是——”
“请将军和在下过招。”我说,“让我领教领教玄家嫡传的功夫。”
周德胜在旁边,那脸一下子白了。
“韩兄弟!”他压低声音,那声音急得很,“你疯了?这是玄将军!是陇右节度副使!是——”
我没理他,只望着玄凝冰。
她站在那儿,望着我,那眼神里有了一种新的东西——是意外,是那种“有点意思”的意外。
然后她笑了。
那笑从嘴角溢出来,从那眼睛里溢出来,在那张三十五岁的脸上,像一朵花开。
“好。”她说,“有胆量。”
她的话音刚落,那拳头就到了。
快。
太快了。
我根本没看清她是怎么动的,只看见那拳头带着风声,往我脸上砸过来。我猛地往旁边一闪,那拳头擦着我的耳朵过去,带起的风刮得我脸皮生疼。
我还没来得及站稳,她的腿又到了。
那腿又长又快,像一根鞭子,从侧面扫过来。我往后一仰,那腿从我胸前扫过,那靴尖几乎蹭着我的衣裳。
我往后退了一步。
又一步。
又一步。
她的拳脚像雨点一样打过来,一拳连着一拳,一腿接着一腿,根本不给我喘息的机会。她那身子虽然高挑丰腴,可动起来却灵活得像一头豹子,那拳脚又狠又准,每一招都奔着我的要害来。她动起来时,那银甲下面的身子起伏得更厉害了——胸前那两座小山随着出拳一颤一颤的,腰肢扭得像风里的柳条,那臀在转身时绷得紧紧的,画出道道圆熟的弧线。
可那弧线里,藏着杀机。
我只能拼命地躲,拼命地挡,拼命地招架。
可挡不住。
她太快了。
太猛了。
太——
我被她一脚扫中小腿,那腿一软,差点跪下去。我踉跄着稳住身子,她的拳头又到了,直奔我面门。我抬手去挡,挡是挡住了,可那拳头的力道震得我整条胳膊都麻了。
我往后退。
再退。
再退。
我已经退到了校场边上,再退就要撞上那些围观的士兵了。
她的攻势还是那么猛,那么快,那么——
我知道,这么下去,我撑不过三十招。
我得想办法。
我一边挡着她的拳脚,一边在脑子里飞快地转着。柔道讲究的是借力打力,是抓住对手的破绽,是利用对手的失误。她虽然厉害,可再厉害的人,也会有破绽。
我等。
我忍。
我一边退,一边等。
终于,机会来了。
她一拳打过来,我往旁边一闪,她那一拳打空,身子微微往前倾了那么一下。
就那么一下。
我动了。
我从她身侧绕过去,绕到她身后。快,极快,快到我自己都不敢相信。我到了她身后,抬起手,往她后腰上轻轻点了一下。
只是一下。
很轻。
轻得像一片羽毛落上去。
然后我故意放慢了动作,让她能反应过来。
她果然反应过来了。
她猛地转过身,那眼睛里的光一下子变得锐利起来,像两把刀。她的手往我胸口一推——不,不是推,是拍,是那种带着内劲的拍。
我被她拍中,整个人往后飞出去,摔在地上,滚了两滚。
背上硌着地上的石子,疼得很。可我没叫,只是躺在那儿,喘着气。
她站在那儿,望着我。
那眼神冷冷的,像冬天的冰。
我挣扎着爬起来,拍了拍身上的土,踉踉跄跄地站到她面前。
我低下头,抱拳。
“将军武艺高强,”我说,“在下甘拜下风。”
她没说话。
就那么望着我。
周围那些围观的士兵,静得出奇。连那风都像是停了,不敢出声。
周德胜在旁边,那脸白得没一点血色,那嘴张着,想说又不敢说。
玄凝冰望着我。
望着我。
望着我。
然后她开口,那声音冷得很。
“跟我来。”
她转身就走。
我愣了一下,赶紧跟上。
周德胜在后面想跟上来,被她的亲卫拦住了。那些银甲兵站在那儿,像一堵墙,把他挡在外面。
我只能自己跟着她,一步一步,穿过那些银甲兵,穿过那些跪着的各部落头人,穿过那面在风里飘的玄字旗,走进一座巨大的帐篷里。
那帐篷大得很,里头点着好几盏灯,照得亮堂堂的。地上铺着厚厚的毡子,毡子上摆着一张矮几,矮几上放着文书、笔墨,还有一把刀。
那刀就放在那儿,刀鞘黑黑的,刀柄上镶着宝石,在灯光下一闪一闪的。
玄凝冰走进帐篷,走到那张矮几后面,转过身来,望着我。
我站在帐篷门口,离她七八步远。
她望着我。
我也望着她。
然后她动了。
她的手往矮几上一探,握住那把刀,“唰”的一声,刀出鞘了。
那刀光在灯光下一闪,亮得晃眼。她提着刀,一步一步,走到我面前。
那刀尖抵在我脖子上。
凉凉的。
我能感觉到那刀尖贴着我脖子上的皮肤,只要她往前轻轻一送,我就没了。
她站在我面前,离得那么近。我这才看清她——三十五岁,正是女人熟透了的时候。那银甲虽然严实,却遮不住她身上那股子熟媚的劲儿。胸前那两座山隔着甲片也能看出形状,随着呼吸微微起伏,像要挣出来似的。腰肢被甲裙勒得细细的,越发显得那胯宽臀圆。她就那么站着,可那身子往前挺着,往后翘着,像一张拉满了的弓,浑身都是力,浑身都是美。
她望着我,那眼睛冷冷的,像两潭结了冰的水。
“说吧,”她说,“为什么要让我?”
我愣了一下。
“将军——”
“别装。”她打断我,“你那一下,明明可以把我打倒。你没用力,只是点了一下。然后你故意放慢动作,让我反应过来。”
她顿了顿,那刀尖往前送了送,扎得我脖子上的皮微微陷进去。
“为什么要让我?”
我望着她,望着这张近在咫尺的脸,望着这双冷冷的眼睛,望着这把抵在我脖子上的刀。
心里那团东西,反倒静下来了。
“将军,”我说,“我实力不足,只能认输。”
她没说话。
就那么望着我。
望着我。
望着我。
然后她嘴角动了动。
那刀,从脖子上移开了。
她把刀收回去,“唰”的一声,插回刀鞘里。她把刀往矮几上一扔,转过身,走到那张毡子上坐下。她坐下时,那身子一矮,胸前那两座小山跟着颤了颤,那臀在毡子上压出一道圆滚滚的弧线。
她抬起头,望着我。那眼睛里的冷,退了一些。换了一种东西——是那种“有点意思”的光。
“懂得人情世故,”她说,“是个滑头。”
我站在那儿,没动。
她伸手,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。
那块表。
我的那块表。
她把那表托在掌心里,对着灯光看。那银色的壳子在灯光下一闪一闪的,那表盘上的数字清清楚楚的,那三根针还在走,一下一下的,走着。
她看了许久。
然后她抬起头,望着我。那眼神,变了。
变得深了。
变得沉了。
变得让人看不懂了。
她开口,那声音低低的,可那低里有沉。
“韩天,”她说,“我问你,这种东西,你怎么会有?”
我望着她。
“将军指的是什么?”
“这东西。”她把那表往上托了托,“这是陛下才有的东西。”
我心里咯噔一下。
陛下的东西?
绍武皇帝?
“这——”我说,“这不是从宫里出来的。这是先父留下的。”
她望着我,那眼睛里的光锐得很。
“先父?”
“是。”我说,“先父当年去波斯做生意,从西洋那边带回来的。传了几辈子,传到我手里。”
她没说话,就那么望着我。
然后她低下头,把那表翻过来,看表背。
我看不见表背上有什么,可我知道,那上面刻着一行字。
那是我的名字。
韩天。
英文的。
还有日期。
我穿越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天。
她看着那表背,看了许久。
然后她抬起头,望着我。那眼神,复杂得很。
“韩天,”她说,“这表背上,刻着你的名字。”
我点点头。
“是。那是先父刻的。”
她望着我。
“跟陛下有什么渊源?”
我心里又是一跳。
陛下。
又是陛下。
“没有渊源。”我说,“草民不敢高攀。”
她没说话,就那么望着我。那眼神,像是在想什么,又像是在等什么。
然后她开口。
“你几岁了?”
我愣了一下。
“二十。”
她点点头。
“二十。”
她把那表收起来,握在手里。她望着我,那嘴角动了动,像是在笑,又像是没在笑。
“这表,”她说,“我收下了。”
我点点头。
“应该的。”
她望着我。
望着我。
望着我。
然后她开口,那声音轻轻的,可那轻里有东西。
“韩天,”她说,“你可知道,送女人刻着你自己名字的表,是什么意思?”
我心里有什么东西一沉。
“将军——”
她没让我说下去。
“当年,”她说,“陛下告诉过我。如果一个男人,把他刻着自己名字的表送给一个女人——那就是他想娶那个女人。”
她顿了顿。
“而你,”她望着我,那眼睛里的光复杂得很,“居然敢向我求婚。”
我脑子里嗡的一声。
求婚?
我?
我张了张嘴,想说什么,可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她望着我这张着嘴愣住的样子,那嘴角动了动,像是想笑。
“不用解释。”她说,“这三十多年,还没有哪个男人敢向我求婚。你是头一个。”
我好不容易找回自己的声音。
“将军,”我说,“我没有那个意思。这表只是——只是我的一片心意。我身份低微,不敢高攀将军——”
我的话还没说完,她的脸色变了。
那笑没了。
那眼睛里,有了一种东西——是不悦,是那种“你这话我不爱听”的不悦。
她望着我,那眼神冷冷的。
“当初陛下还说过,”她说,“如果一个男人说他自己配不上那个女人,那就是他在嫌弃那个女人。”
她顿了顿。
“说吧,”她说,“你是不是嫌弃我老?”
我站在那儿,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嫌弃她老?
她老吗?三十五岁,不高不矮,不胖不瘦,那脸那身子,放到哪儿都是一等一的美人。那胸前鼓鼓的,那腰细细的,那臀圆圆的,那腿长长的,浑身上下透着熟透了的风情。她老什么老?
可她说的不是这个。
她说的是——陛下说的。
陛下说的。
绍武皇帝说的。
送刻着名字的表,是想娶她。
说配不上,是嫌弃她老。
这两句话——
这两句话怎么这么——
这么耳熟?
不,不是耳熟。
是现代。
是那种只有现代人才会说的话。
我站在那儿,望着她,望着她手里那块表,望着她那张脸,那双眼睛。
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在转。
在转。
在转。
转得越来越快。
转得越来越乱。
转得——
绍武皇帝。
韩月。
七十多岁。
打下这大半天下的男人。
他怎么会说这种话?
这种——这种只有从那个世界来的人才会说的话?
送表求婚。
嫌弃就是嫌老。
这是二十一世纪的梗。
是那个世界的梗。
他怎么知道?
除非——
除非他也是——
我脑子里轰的一声。
穿越者。
绍武皇帝韩月,也是穿越者。
我站在那儿,脑子里那团东西还在炸着,可她的目光还在我身上,等着我回答。
嫌弃她老?
我望着她——三十五岁,不高不矮,不胖不瘦,那脸那身子,放到哪儿都是一等一的美人。那银甲下面,是常年习武才有的身板,肩宽背厚,腰细腿长,那胸前的甲高高隆着,那腰间的甲收得紧紧的,那臀在甲裙下面圆鼓鼓的,像两座小山。她哪里老了?
可我说的不是这个。
我深吸一口气,望着她的眼睛。
“将军,”我说,“我不是嫌弃你老。”
她没说话,就那么望着我,等着。
“我有妻子了。”
那五个字说出来,她的眼睛动了一下。
只是一下。
很快。
可我看清了。
她站在那儿,望着我,那眼神里有一种东西——是意外,是那种“居然还有这种事”的意外。
然后她笑了。
那笑不是刚才那种冷笑,也不是比武前那种欣赏的笑。那是一种很奇怪的笑——有点愣,有点懵,有点像是听见了什么她这辈子都没听过的话。
“你有妻子了?”
我点点头。
“是。”
她望着我。
望着我。
望着我。
然后她哈哈大笑起来。
那笑声在帐篷里响着,震得那几盏灯的火苗都跟着跳。她笑得弯下腰,笑得那胸前的甲一颤一颤的,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。她弯腰时,那胸前两座小山晃得厉害,那腰肢折成一道弯,那臀往后翘得更高了,整个人像一弯熟透的月牙儿。
我站在那儿,不知道该说什么,就那么看着她笑。
她笑了好一会儿,才慢慢收住。她直起腰,望着我,那眼睛里还带着笑出来的水光。
“韩天,”她说,“你可知道,除了陛下,你是第二个跟我说这种话的男人。”
我心里一动。
“什么意思?”
她走到矮几旁边,坐下,伸手示意我坐下。
我在她对面的毡子上坐下,隔着那张矮几,望着她。灯光从侧面照过来,把她那熟透了的身子勾出一道金边——那胸前高高地隆着,那腰肢深深地凹着,那臀在身后压出一道圆滚滚的弧线。
她望着我,那眼神里有一种东西——是回忆,是那种“想起很多年前的事”的光。
“听我母亲说,”她开口,“陛下年轻的时候,就是这个样子。”
我竖起耳朵。
“那时候,陛下刚起兵不久,身边只有一个女人——就是现在的皇后娘娘,妇姽。那时候皇后娘娘比他大十七岁,可陛下眼里只有她,别的女人碰都不碰。”
大十七岁。
我心里算了一下。
那皇后今年得九十多了?
“后来呢?”我问。
她望着我。
“后来,发生了很多事。”她说,“具体的,我也不清楚。只知道后来我姨母——就是现在的玄贵妃——也入了宫。再后来,我母亲也——”
她顿了顿,没往下说。
可我听懂了。
玄悦。
玄凤。
她们都是后来才入宫的。
也就是说,皇帝年轻时,确实只守着那一个比他大十七岁的女人。
我坐在那儿,心里那团东西翻得更厉害了。
这皇帝——
他真的也是穿越者?
她望着我,那眼神又变了。
变得冷了。
变得硬了。
变得像刚才那把刀抵在我脖子上时的样子。
“韩天,”她说,“看起来,我必须把你带回皇都了。”
我心里一沉。
“皇都?”
“对。”她说,“京城,长安。”
我张了张嘴。
“将军,我——”
她打断我。
“你是我三十多年来,头一个让我看进眼里的男人。”她说,那声音不高不低,可那不高不低里有种不容置疑的东西,“我必须把你带回去,给我母亲看看,给陛下看看。”
我慌了。
“将军,”我说,“我不能去。我家里还有妻子,还有——还有部族要照顾。狼部六万多人,都指望着我。还有金川部那边,我收留了甲洛的侄女,他迟早要来找麻烦——”
她抬起手,打断我。
那动作轻轻的,可那轻轻里有威。
“金川部?”她说,“甲洛?”
我点点头。
她嘴角动了动,像是不屑。
“一个小小的金川部,也值得你挂在嘴上?”
我没说话。
她望着我,那眼神里有一种东西——是那种“你太小看我了”的光。
“韩天,”她说,“你听好了。”
我望着她。
“你是我玄凝冰看上的人。”她说,“从今往后,你的事,就是我的事。金川部敢动你,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”
我心里那团东西动了一下。
可我还是摇头。
“将军,我真的不能去。我——我才二十岁——”
她脸色变了。
那眼睛里的光一下子冷下来。
“二十岁?”她说,“你果然还是嫌弃我老。”
“不是——”
“当初皇后娘娘比陛下年长十七岁,陛下都不嫌弃。”她打断我,那声音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东西——是不悦,是委屈,是那种“你这人怎么这样”的恼,“你一个小小的狼部指挥使,居然敢嫌弃我这个陇右节度副使?”
我张着嘴,想解释,可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她站起来。
我也跟着站起来。
她走到我面前,站在那儿,居高临下地望着我。她比我高出半个头,这么站着,我得仰着脸才能看见她的眼睛。这么近的距离,她身上那股子熟透了的气息直往我鼻子里钻——那胸前两座山几乎要贴到我身上,那腰肢细得像能一手握住,那臀在身后撑得满满的,绷得紧紧的。
那眼睛里的光,复杂得很。
有恼。
有不解。
还有一种东西——是那种“你这人有点意思”的光。
“韩天,”她说,“我再问你一次。你跟我去不去?”
我望着她,望着这张近在咫尺的脸,望着这双等着我回答的眼睛。
心里那团东西翻来覆去。
妈。
阿依兰。
丹珠。
狼部那六万多人。
那些刚开的梯田,那些新修的房,那些刚走上正道的日子。
她们都在等我。
等我带着那个名分回去。
等我回去。
我开口。
那声音有点干。
“将军,我——”
话还没说完,她笑了。
那笑不是刚才那种冷笑了。是一种很奇怪的笑——有点无奈,有点欣赏,还有一种“你这人我拿你没办法”的宠。
“行了,”她说,“别说了。”
她转过身,走回矮几后面,坐下。坐下时,那臀在毡子上压出一道圆滚滚的弧线,半天都没散。
她望着我。
“韩天,”她说,“我给你三天时间。”
我愣了一下。
“三天?”
“对。”她说,“三天之内,你把你那些事处理好。狼部的事,金川部的事,你那个妻子的事——”
她顿了顿。
“三天之后,你跟我回皇都。”
我站在那儿,心里那团东西跳得厉害。
“将军——”
她抬起手,打断我。
“你放心,”她说,“你那个妻子,我不会动她。你那些部族,我也不会不管。等到了皇都,见了陛下,把事情办妥了——你想回来,随时可以回来。”
她望着我,那眼神里有一种东西——是那种“我说到做到”的保证。
我站在那儿,望着她。
心里那团东西,慢慢地,慢慢地,静下来。
三天。
我只有三天。
三天之内,要把所有事情都处理好。
然后跟她去皇都。
去见那个——可能也是穿越者的皇帝。
我深吸一口气。
“好。”
她点点头。
“去吧。”
我转过身,往帐篷门口走去。
脚下是厚厚的毡子,踩上去软软的,没有声音。那几盏灯在我身后亮着,把我的影子投在帐篷的布壁上,长长的,一晃一晃的。
走到门口,我的手刚碰到那帐门的布帘——
“韩天。”
她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
我停下。
没回头。
就那么站着,背对着她。
“如果你敢不回来——”
她顿了顿。
那声音从身后传来,不高不低,可那不高不低里,有一种东西让我后背发凉。
“我就屠了你的部族。”
我站在那儿,手还抓着那布帘,可那手指,僵住了。
屠了你的部族。
狼部。
六万多人。
妈。
阿依兰。
丹珠。
那些刚学会种地的男人,那些刚穿上丝绸的女人,那些刚念上“人之初”的孩子——
屠了。
我慢慢转过身。
她坐在那张矮几后面,灯影照在她脸上,明明暗暗的。那脸看不清表情,只看见那双眼睛,在昏暗里亮亮的,像两点鬼火。
她就那么望着我。
没说话。
没笑。
就那么望着。
我望着她,心里那团东西翻来覆去地滚。
我开口,那声音有点干。
“将军放心。”
她点点头。
“去吧。”
我转过身,掀开那布帘,走了出去。
帐外的风一下子扑到脸上,凉凉的,把我从那种恍惚里吹醒过来。我站在那儿,深深地吸了口气,才迈步往前走。
那些银甲兵还在,站在帐篷四周,像一尊尊银色的雕像。他们望着我,那眼神里有一种东西——是好奇,是打量,还有一种说不清的、让人不自在的光。
我穿过他们,穿过那面在风里飘的玄字旗,往校场那边走。
周德胜正在校场边上等着,看见我出来,赶紧迎上来。
“韩兄弟!”
他跑到我面前,那脸上带着一种奇怪的表情——是兴奋,是紧张,还有那种“你到底怎么样”的问号。
“怎么样?”他压低声音,“玄将军跟你说什么了?”
我望着他,望着这张黑黑的、满是关切的脸。
“她要我去皇都。”
他愣了一下。
“皇都?”
我点点头。
“长安。”
他张了张嘴,那眼睛瞪得大大的。
“长安?”他说,“去长安干什么?”
我摇摇头。
“不知道。”
他站在那儿,那脸上的表情变了几变。然后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,把我拉到旁边一个没人的角落。
“韩兄弟,”他说,那声音压得低低的,可那低低里有种掩不住的兴奋,“玄将军这是看上你了!”
我望着他。
“看上我?”
“对!”他拍着我的胳膊,“你不知道,玄家在大夏朝是什么地位!”
我没说话,等着他说下去。
他往四周看了看,确认没人,才凑到我耳边,那声音低得像蚊子叫。
“玄家,是大夏朝排名前三的世家。”
我心里动了一下。
“前三?”
“对。”他说,“头一家当然是皇家,韩家。第二家,是皇后娘娘的娘家,妇家。第三家,就是玄家。”
他顿了顿。
“玄家一门三凤,你听说过吧?”
我点点头。
“那你知道,玄家在大夏朝有多大的势力不?”
我摇摇头。
他伸出一根手指。
“玄素,中央军校校长。从她手底下出来的将军,没有一千也有八百。那些将军如今遍布天下,哪个见了玄家的人不得恭恭敬敬的?”
又伸出一根。
“玄悦,皇贵妃,燕王的生母。燕王是大将军王,手握重兵,是陛下最信任的儿子。”
第三根手指。
“玄凤,当年帮着陛下废了虞昭,是陛下登基的功臣。虽说如今不怎么出来了,可她在军中的威望,还在那儿。”
他望着我,那眼睛亮得厉害。
“玄凝冰,就是玄凤的小女儿。她自己就是陇右节度副使,管着这么大一片地方的兵马。她要是看上你了——”
他顿了顿,那声音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羡慕。
“韩兄弟,你们狼部,要起飞了。”
我站在那儿,听着他说这些话,心里那团东西翻来覆去。
起飞。
被玄家看上。
去皇都。
见皇帝。
还有她那句话——
如果你敢不回来,我就屠了你的部族。
我抬起头,望着天边那渐渐沉下去的太阳。那太阳红红的,大大的,把半边天都染成了血色。
周德胜在旁边,还在说着什么。我没听进去。
我只想着那三个字。
不回来。
屠了。
我深吸一口气。
“德胜。”
他停下来,望着我。
“我得回去一趟。”
他愣了一下。
“回去?回哪儿?”
“狼部。”我说,“三天之内,我得把那边的事情安排好。”
他点点头。
“应该的应该的。那你快去快回。玄将军这边,我帮你盯着。”
我拍了拍他的肩,没再说什么,转身往客栈走。
阿勒他们还在客栈等着。
我走得很快,几乎是在跑。
天边那血色越来越浓,把那西宁城的城墙、那房屋、那街道,都染得红红的。
我跑在那一大片红里,心里只有一个念头。
三天。
只有三天。
我知道三天不可能回狼部。
从西宁到狼部,快马加鞭也得走上七八天。就算我不眠不休地赶路,来回也得半个月往上。更不用说还要处理部族里那些事——安抚人心,交代后路,跟阿依兰和丹珠解释这一切。
三天。
她给我的三天,不过是让我想清楚,不过是给我一个体面。
我站在客栈门口,望着天边那血色一点一点沉下去,心里那团东西翻来覆去地滚。阿勒在身后站着,不敢出声,只是那么站着,等我开口。
过了许久,我转过身。
“阿勒。”“在。”“明天一早,你带两个人,回狼部。”他愣了一下。
“大人,您不回去?”我摇摇头。
“我回不去。”我说,“你回去,告诉夫人和丹珠——我有要事,要去一趟长安。短则三五个月,长则一年半载。让她们别担心,好好守着部族,等我回来。”阿勒张了张嘴,想说什么,又咽了回去。
我拍了拍他的肩。
“去睡吧。明天还要赶路。”他点点头,转身走了。
我一个人站在那儿,站了许久。
第二天一早,我送走了阿勒他们,转身去找周德胜。
周德胜正在营房里喝早茶,看见我进来,赶紧站起来。
“韩兄弟?这么快就回来了?不是说要回狼部吗?”我在他对面坐下。
“回不去。”我说,“太远了。”他点点头,没多问。
我望着他。
“德胜,我有事求你。”他愣了一下,然后笑了。
“说。咱们兄弟,什么求不求的。”“我不在的这段时间,”我说,“狼部那边,你得帮我盯着点。派些人马,时不时去巡逻一下,让那些心怀不轨的人知道——狼部有靠山,动不得。”他点点头。
“这个好办。我回头就安排。”我又说:“还有金川部。甲洛迟早要来找麻烦。我想给他送点东西,稳住他一时。等我从长安回来,再跟他算账。”周德胜想了想。
“送什么?”“厚礼。”我说,“茶叶、布匹、铁器——能送多少送多少。以我狼部镇守使的名义送,就说我希望两家和好,往后和平相处,互不侵犯。”周德胜望着我,那眼神里有一种东西——是佩服,是那种“你这人想得真远”的光。
“韩兄弟,”他说,“你这脑子,转得是真快。”我苦笑了一下。
“没办法。人命关天。”他点点头。
“你放心。这事我帮你办。礼单我替你拟,东西我替你备,人我替你派。保证办得漂漂亮亮的。”我站起来,冲他抱了抱拳。
“德胜,大恩不言谢。”他也站起来,拦住我的手。
“别。”他说,那脸上带着笑,“韩兄弟,你往后要是真成了玄家的姑爷,别忘了提携提携我就行。”我愣了一下。
“什么姑爷?”他挤了挤眼睛。
“装什么装?玄将军看你的眼神,当我没看见?我跟你说,玄家的姑爷,那可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福分。你这一去,八成就是入赘玄家了。”我站在那儿,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他拍拍我的肩。
“去吧去吧。别让人家等急了。”我望着他,心里那团东西热热的。
“德胜,保重。”“保重。”从营房出来,我直接往总督府走。
玄凝冰已经搬进了西宁总督府。那是西宁城里最大的宅子,原先是给驻西宁的钦差大臣住的,如今腾出来给她用。
我走到总督府门口,那些银甲兵还在,站在大门两侧,像两排银色的雕像。他们看见我,眼神里有一种东西——是认得,是那种“就是这个人”的光。
为首的上前一步。
“韩指挥使?将军吩咐过,您来了直接进去。”我点点头,跟着他往里走。
穿过大门,穿过前院,穿过一道月洞门,走到一座小院门口。那院门开着,里头种着几竿竹子,在风里沙沙地响。
“将军就在里头。”他说完,转身走了。
我站在院门口,深吸一口气,迈步进去。
她正站在院子里。
换下了那身银甲,穿着一身月白的衣裙,那料子软软的,滑滑的,贴着身子,把她那身段勾得清清楚楚。那胸前鼓鼓的,把那月白的衣料撑得高高的,像两座小山;那腰细细的,被一根同色的腰带轻轻束着,越发显得不盈一握;那臀圆圆的,在裙子里绷得紧紧的,随着她微微的动作,轻轻晃动。
她就那么站在那儿,站在那几竿竹子旁边,阳光透过竹叶洒在她身上,斑斑驳驳的。
她听见脚步声,转过头来。
那眼睛落在我身上,先是一愣,然后——亮了。
那亮是从眼底深处透出来的,像一盏灯突然被点燃。她望着我,那嘴角动了动,想笑,又像是忍住了。可那笑意还是从眼角溢出来,从眉梢溢出来,从那张三十五岁的脸上溢出来,藏都藏不住。
她望着我。
我望着她。
我们就那么望着,望了那么几息。
然后她开口,那声音平平的,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。
“回来了?”我点点头。
“回来了。”她又问:“事情都办妥了?”“托将军的福,”我说,“都办妥了。”她点点头。
“那就好。”她转过身,往屋里走。
“进来坐吧。”我跟在她身后,往屋里走。她走得不快,一步一步的,那腰肢轻轻扭着,那臀在裙子里一荡一荡的,像两弯月牙儿在水里晃。那月白的衣裙随着她的步子微微飘动,把那熟透了的身子勾得若隐若现。
我跟着她,进了屋。
屋里不大,收拾得干干净净的。靠窗摆着一张矮几,矮几上放着茶具。她走到矮几旁边,坐下,伸手示意我坐。
我在她对面的蒲团上坐下,隔着那张矮几,望着她。
阳光从窗子里透进来,照在她身上,把那月白的衣裙照得有些透。我能隐隐约约看见那衣裙下面,那两条长长的腿并着,那膝盖圆圆的,那小腿细细的,一直延伸到裙摆里头。
她提起茶壶,给我倒了一杯茶。
那动作轻轻的,缓缓的,像是怕惊着什么似的。
她把茶盏推到我面前。
“喝茶。”我端起茶盏,抿了一口。
她望着我,那眼神在我脸上转着。
“狼部那边,安排好了?”“安排了。”我说,“我让人回去报信了。”“你那个妻子——她叫什么来着?”“阿依兰。”她点点头。
“阿依兰。”她重复了一遍,那两个字从她嘴里出来,带着一种说不清的味道,“她——好看吗?”我愣了一下,抬起头,望着她。
她也望着我,那眼睛里有一种东西——是好奇,是探究,还有一点点别的什么。
“好看。”我说。
她点点头。
没再问了。
就那么坐着,望着我。
我也坐着,望着她。
屋里静静的,只有窗外的竹叶在风里沙沙地响。
过了许久,她开口,那声音低低的。
“韩天。”“在。”“你就不好奇,我带你去皇都,是做什么?”我望着她。
“将军说,去见陛下。”她点点头。
“是去见陛下。可你知道,为什么要见陛下吗?”我摇摇头。
她望着我,那眼神里有一种东西——是那种“你这人怎么这么不开窍”的无奈。
然后她叹了口气。
“韩天,”她说,“你这个人,是真不懂,还是装不懂?”我没说话。
她望着我,望着我,望着我。
然后她开口,那声音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东西——是羞,是恼,是那种“这话非得我先说”的委屈。
“入赘玄家,”她说,“你愿不愿意?”我心里那团东西猛地一跳。
入赘玄家?
她见我没说话,那脸上微微红了一下。只是一下,很快,可我看见了。
她别过脸去,望着窗外的竹子,那声音从侧脸传来。
“入赘我们玄家,是很好的。”她说,“玄家不会亏待自己人。”我没说话,等着她说下去。
她顿了顿,又开口,那声音慢慢的,像是在回忆什么。
“我父亲,当年就是江南的贡生,考中过探花郎。长得好看,又有才学,被我母亲看上了。”她转过头来,望着我。
“你知道我母亲是谁吗?”我摇摇头。
“玄凤。”她说,“当年跟着陛下打天下,出生入死,立下过汗马功劳的玄凤。她看上我父亲,就把人带回了玄家。”她望着我,那眼睛里有一种光。
“我父亲一开始也不愿意。他是读书人,功名在身,前程似锦,入赘世家,传出去不好听。可我母亲不管那些。她认定了的事,谁也拦不住。”她顿了顿。
“后来呢?”“后来,”她说,“我父亲入了朝,有玄家做后台,一路做到司礼监祭酒、理藩院主事。三品大员。”她望着我。
“我父亲常跟我说,当年他要是犟着不来,如今还在江南当个穷教书先生。哪有今日的风光?”我没说话。
她继续说:“我母亲和我父亲,成亲三十多年,感情一直很好。我上头四个哥哥,都是他们一起生的。我们兄妹五个,从小到大,从没红过脸。逢年过节,一家人聚在一起,热热闹闹的。我父亲常说我母亲是他的贵人,我母亲说我父亲是她这辈子最好的眼光。”她说着,那嘴角微微翘起来,像是在笑。
那笑里,有一种东西——是羡慕,是向往,是那种“我也想要这样的日子”的光。
她望着我。
“韩天,我今年三十五了。”我没说话。
“这三十五年来,求亲的人踏破了门槛。有王公贵族的公子,有世家大族的嫡子,有手握重兵的将军,有才高八斗的状元。我一个都没看上。”她顿了顿。
“你是第一个。”我心里那团东西翻了一下。
她望着我,那眼神里有一种东西——是认真,是那种“我没开玩笑”的认真。
“我知道你有妻子。我不在乎。”她说得很轻,可那轻里有一种沉。
“你是狼部的镇守使,她是狼部的女人。你在狼部有家,有部族,有放不下的人。我不让你丢下他们。”她望着我。
“等见了陛下,把事情办妥了,你想回来,随时可以回来。想带她一起来,也行。玄家容得下她。”我听着她说这些话,心里那团东西翻来覆去。
她见我不说话,那脸上的表情变了一下。
“韩天,”她说,那声音里带着一点不确定,“你——你不愿意?”我抬起头,望着她。
望着这张三十五岁的脸,望着这双等着我回答的眼睛,望着这个站在我面前、把一辈子的话都说尽了的人。
我开口。
“将军——”她打断我。
“叫我凝冰。”我愣了一下。
“凝冰。”她点点头,那嘴角微微翘起来。
我望着她,望着她那张脸上那一点点藏不住的笑意,心里那团东西忽然就静下来了。
“凝冰,”我说,“我不是不愿意。”她望着我,等着。
“我只是——”我顿了顿,“我只是没想到,你会看上我。”她愣了一下,然后笑了。
那笑从嘴角溢出来,从那眼睛里溢出来,从那脸上溢出来,像一朵花开。
“你这人,”她说,“是真傻还是装傻?”我没说话,只是望着她笑。
她也望着我笑。
我们就那么望着,望着,望着。
阳光从窗外透进来,洒在她身上,把她那月白的衣裙照得亮亮的,把她那熟透了的身子勾得柔柔的,把她那张三十五岁的脸照得暖暖的。
她坐在那儿,望着我,那眼睛里的光,软得像一汪水。
我坐在那儿,望着她,心里那团东西,慢慢地,慢慢地,化成了一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