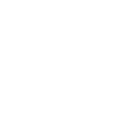24.京城的大学
一夜未眠。
不是不想睡,是睡不着。
躺在床上,闭着眼,脑子里翻来覆去的全是事儿。玄凤那双锐利的眼睛,钱寅一满意的笑容,玄襄海爽朗的大笑,玄襄城那难得的一点头,还有玄凝冰送我出门时那软软的目光。
可最多的,还是草原上的那些脸。
妈。阿依兰。丹珠。还有狼部那些叫不出名字的人——那些刚学会种地的男人,那些刚穿上丝绸的女人,那些刚念上“人之初”的孩子。
她们在等我。
等我带着那个名分回去。
等我回去。
可我现在躺在这儿,躺在这间豪华的客房里,躺在这张软软的床上,离她们几千里远。
金川部的甲洛,不会等。
他不会等我回去,不会等我安排好一切,不会等我拿到什么名分。他只知道,我收留了他的侄女,打了他的脸,抢了他的人。他会来报仇的。迟早的事。
而狼部,那六万多人,拿什么挡他?
就靠那些刚放下刀、刚拿起锄头的牧民?
就靠那些刚学会“人之初”、还不会“性本善”的孩子?
我翻了个身,望着窗外的月光,心里那团东西翻来覆去地滚。
一夜,就这么过去了。
第二天早上,我顶着一双黑眼圈爬起来。
洗漱完毕,换好衣裳,推门出去。
院子里,阳光正好。竹叶上挂着露珠,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水池里的锦鲤悠闲地游着,红的黄的白的,把池水染得五彩斑斓。
有仆人过来,弯了弯腰。
“韩公子,老爷和夫人请你去正厅用早膳。”我点点头,跟着他走。
正厅里,人已经到齐了。
钱寅一坐在主位上,端着一盏茶,慢慢地喝着。玄凤坐在他旁边,换了一身深青色的长袍,头发依旧一丝不苟地盘着,那脸上的笑比昨晚柔和了些。
玄凝冰坐在下首,看见我进来,眼睛亮了一下,嘴角微微翘起来。
玄襄海和玄襄河也在,看见我,都笑着点了点头。玄襄城不在,大概是回军营了。
我上前,给钱寅一和玄凤行了礼。
“父亲,娘。”钱寅一笑眯眯地点头。
“来了?坐,坐。”玄凤也点点头,那眼神在我脸上转了一圈。
“昨晚没睡好?”我心里一动。
这老太太,眼睛真毒。
我点点头。
“是。想了一些事。”她没再问,只是指了指旁边的座位。
“坐吧。先吃饭。”早膳很丰盛。粥有四五种,小菜七八碟,还有包子、花卷、油条、豆浆,摆了满满一桌。我默默地吃着,心里却一直转着那些事。
吃到一半,我终于忍不住了。
我放下筷子,抬起头,望着玄凤。
“娘,我有个事想问。”玄凤也放下筷子,望着我。
“说。”我斟酌了一下措辞。
“我在狼部那边,有个官职——狼部镇守使。是驻藏大臣衙门册封的。可我听说,朝廷这边,还有更大的官职,比如——青海护边使?”玄凤的眼睛动了一下。
只是一下。
很快。
“青海护边使,”她说,“你从哪儿听说的?”“周德胜。西宁城的那个守备。”她点点头。
“那是驻藏大臣的属官,管着青海那一带的边务。确实是个要紧的职位。”我望着她。
“我想拿到这个职位。”她没说话,就那么望着我。
我继续说:“不是为了我自己。是为了狼部。我管着六万多人,可我的名分只是镇守使,还是驻藏大臣衙门给的。在朝廷这边,根本不算什么。金川部的甲洛要是来找麻烦,我拿什么挡他?就靠狼部那些刚放下刀的牧民?”她听着,那眼神没有什么变化。
我顿了顿,又说:“还有,我在狼部那边,正在推行汉化。让他们学种地,学手艺,念书识字,按朝廷的法子过日子。可这些事,光靠我一个人不够。得有朝廷的支持,得有正式的名分,得有人给我撑腰。”我说完,望着她,等着。
屋里静了一下。
玄襄海和玄襄河对视了一眼,没说话。玄凝冰望着我,那眼神里有一种东西——是担心,是那种“你别太着急”的担心。
玄凤端起茶盏,慢慢地喝了一口。
放下。
然后她开口,那声音不高不低,可那不高不低里,有一种沉。
“韩天,你的想法,是好的。推行汉化,让那些部族归心,这是陛下这些年一直在做的事。你能想到这个,说明你是个有脑子的人。”我心里微微松了口气。
可她接着说:“可你知道,如今的大夏朝,和你以前知道的那个大虞朝,有什么不一样吗?”我愣了一下。
“什么?”她望着我,那眼神锐利得很。
“大虞朝的时候,做官靠什么?靠门第,靠关系,靠送钱。谁家的门第高,谁的关系硬,谁送的钱多,谁就能当官。当多大的官,全看你背后站着谁。”她顿了顿。
“可那是以前的事了。”她站起来,走到窗前,背对着我。阳光从窗外透进来,把她那满头的白发染成金色。
“陛下登基以后,第一件事,就是改了这规矩。”她转过身,望着我。
“如今的大夏朝,所有大小官员,逢进必考。”逢进必考。
这四个字,像一块石头,砸在我心里。
“什么意思?”我问。
她走回来,坐下,望着我。
“意思就是,想当官,先得考试。不是考一场,是考好几场。”她伸出一根手指。
“第一场,是大学入学考试。由考试院主持,全国统一考。考上了,才能进大学念书。”第二根手指。
“进了大学,念三年,拿到学位。然后才能参加第二场——帝国公职人员考试。”第三根手指。
“考过了公职人员考试,才有资格进入内政部的名单。然后由内政部统一安排职位——从最底层的小吏做起,一步一步往上爬。”她望着我。
“你现在,既没有大学文凭,也没参加过公职人员考试。别说青海护边使,就是最普通的一个九品小吏,你也当不了。”我听着,心里那团东西一点一点地往下沉。
“可我已经是狼部镇守使了——”“那是驻藏大臣衙门给你的。”她打断我,“那是边地的事,朝廷管不着。可你要真想进朝廷的体系,真想拿到朝廷的名分,真想有朝廷给你撑腰——那就得按规矩来。”她顿了顿。
“规矩,是陛下定的。谁也改不了。”我坐在那儿,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逢进必考。
大学。
文凭。
考试。
这——这不是我那个世界的规矩吗?
那个穿越者前辈,把他那个世界的规矩,搬到了这里。
可对我现在来说,这规矩——太慢了。
三年大学,然后公职人员考试,然后从底层小吏做起,一步一步往上爬——等到我能爬到能保护狼部的位置,黄花菜都凉了。
甲洛不会等我三年。
金川部的人,不会等我三年。
那些盯着狼部、想趁火打劫的人,不会等我三年。
我抬起头,望着玄凤。
“娘,就没有别的办法?”她望着我,那眼神里有一种东西——是理解,是那种“我知道你急”的理解,可那理解里,也有无奈。
“没有。”那两个字,沉沉的,像两座山。
我坐在那儿,心里那团东西翻来覆去地滚。
玄凝冰在旁边,轻轻地碰了碰我的胳膊。
“韩天……”我没说话。
就那么坐着。
过了好一会儿,我站起来。
“父亲,娘,我吃好了。先告退。”钱寅一望着我,那眼神里有担心。玄凤点点头,没说话。
我转过身,往外走。
玄凝冰跟了出来。
她追上我,拉住我的袖子。
“韩天!”我停下脚步,转过身,望着她。
她也望着我,那眼神里有担心,有心痛,还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。
“你别急,”她轻轻说,“会有办法的。”我望着她,望着这张三十五岁的脸,望着这双柔柔的眼睛。
“凝冰,”我说,“我想见陛下。”她愣住了。
那眼睛瞪得大大的,像是听见了什么不可思议的话。
“什么?”“我想见陛下。”我又说了一遍。
她张了张嘴,想说什么,可没说出来。
过了好几息,她才找回自己的声音。那声音压得低低的,像是怕被什么人听见。
“你疯了?”我望着她。
“我没疯。”“没疯?”她的声音还是那么低,可那低里有一种急,“陛下怎么是你想见就能见的?你知道见陛下有多难吗?”她顿了顿,那声音更低了。
“就连我母亲——她是开国功臣,是近卫军统领,是陛下的老部下——一年也见不了陛下几回。寻常的官员,一辈子都未必能见陛下一面。你——你凭什么?”我望着她,没说话。
就那么望着她。
她见我不说话,那脸上的表情更急了。
“韩天,你到底在想什么?”我低下头,望着她手腕上那块表。
那块表,正戴在她腕上。银色的壳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,表盘上的三根针还在走,一下一下的。
我伸出手,轻轻指了指那块表。
“凭这个。”她愣了一下。
低头望着自己腕上的表,又抬起头望着我,那眼神里满是茫然。
“这个?”“对。”我说,“这块表,和我给陛下的那块,是一样的。”她没说话。
就那么望着我。
望着我。
望着我。
然后她噗嗤一下,笑出声来。
那笑来得突然,像一阵风刮过,把她脸上那些担心、着急、茫然,全刮走了。她笑得弯下腰,笑得那胸前的衣裳一颤一颤的,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。
我站在那儿,不知道该说什么,就那么看着她笑。
她笑了好一会儿,才慢慢收住。她直起腰,望着我,那眼睛里还带着笑出来的水光。
“韩天小朋友,”她说,那声音里带着笑,“你——你是认真的?”我点点头。
“认真的。”她又笑了。
那笑不是嘲笑,是一种——哭笑不得,是那种“你这人怎么这么天真”的无奈。
她伸手,在我脸上轻轻拍了拍,像拍一个不懂事的孩子。
“小朋友,你认为陛下会因为这种小事就见你吗?”我望着她。
“这不是小事。”“怎么不是小事?”她说,“你那块表,和陛下的是同款——可那又怎么样?陛下每天要处理多少大事?边关的战事,朝中的政务,各地的灾情,百官的奏折——那些才是大事。你一个狼部镇守使,想凭一块表就见陛下——你觉得可能吗?”我听着她这些话,心里那团东西翻来覆去。
她说得对。
站在她的角度,站在这个世界的角度,这确实是一件小事。
一块表。
一块和陛下同款的表。
这算什么?
可她知道吗?
这块表背后,是什么?
是另一个世界。
是那个和陛下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人。
是那种“老乡见老乡”的缘分。
可这些话,我没法跟她说清楚。
我站在那儿,望着她,心里那团东西堵得慌。
她见我不说话,那脸上的笑慢慢收住了。
她望着我,那眼神变得柔和起来。
“韩天,”她轻轻说,“我知道你急。知道你担心狼部,担心你的家人。可这事急不得。”她握住我的手。
“你先住下来,慢慢想办法。我帮你打听打听,看有没有别的路子。实在不行,等我娘下次进宫的时候,让她帮忙递个话。总会有办法的。”我望着她,望着这张关切的脸,望着这双柔柔的眼睛。
心里那团东西,堵得更厉害了。
可我还是点了点头。
“好。”她笑了,那笑里有一种东西——是放心,是那种“你总算听劝了”的欣慰。
她松开我的手。
“你先回去歇着。晚上我让人送些书过来,给你解闷。”我点点头,转身往西厢走。
走了几步,又停下。
回过头,望着她。
她还站在那儿,站在那满院的阳光下,望着我。那月白色的长裙在风里轻轻飘着,把那熟透了的身子勾得若隐若现。
我望着她,心里忽然涌起一阵说不清的念头。
“凝冰。”“嗯?”“谢谢你。”她愣了一下,然后笑了。
那笑从嘴角溢出来,从那眼睛里溢出来,从那张三十五岁的脸上溢出来,像一朵花开。
“谢什么?傻瓜。”她转过身,走了。
我站在那儿,望着她的背影,望着那月白色的长裙在阳光下一点一点远去,消失在院门后头。
然后我转过身,继续往西厢走。
心里那团东西,翻来覆去地滚。
见陛下。
我一定要见陛下。
不是为了青海护边使,不是为了狼部,甚至不是为了阿依兰她们——是为了我自己。
为了见一见那个和我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人。
为了问问他,你是怎么来的?你是怎么过的?你是怎么——在这陌生的世界,活了三十多年?
可怎么见?
她说了,陛下不是想见就能见的。
就连玄凤,一年也见不了几回。
我一个狼部镇守使,凭什么?
我低着头,慢慢地走着。
走着走着,忽然停下脚步。
抬起头,望着天上那轮太阳。
阳光刺眼,晃得人眼睛发酸。
我眯着眼,望着那太阳,心里那团东西忽然亮了一下。
表。
那块表。
它不只是同款。
它上面刻着我的名字。
刻着我穿越过来的日期。
如果——如果陛下真的是穿越者,如果他看见那块表,看见那上面的字——他会懂的。
他一定会懂的。
可问题是,怎么让他看见那块表?
怎么把表送到他面前?
怎么让他知道,这世上还有另一个和他一样的人?
我站在那儿,望着太阳,想了很久。
然后我低下头,继续往西厢走。
走得慢。
一步一步的。
心里那团东西,还在翻。
可那翻里,有了一点光。
一点小小的、微弱的光。
我问玄凝冰:“既然见不了陛下,那我这几天在京城做些什么?就这么待着,当个吃软饭的小白脸吗?”她愣了一下。
然后那双眼睛弯成了月牙儿。
她张开双臂,一把抱住我,抱得紧紧的。那胸前两座小山压在我身上,软软的,热热的,带着一股淡淡的香。她把脸埋在我肩窝里,蹭了蹭,像一只餍足的猫。
“可以啊!”那声音闷闷的,可那闷里满是笑,“你就好好陪我嘛!陪我逛街,陪我吃饭,陪我看戏,陪我逛园子——我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看上个男人,你就当几天小白脸怎么了?”我被她抱得喘不过气来,挣扎着往外推。
“喂——放开——我快憋死了——”她不肯放,反而抱得更紧。
“不放!好不容易逮着的!”我费了好大的劲,才从她那两条胳膊里挣脱出来。我喘着气,整理着被她弄乱的衣裳,瞪着她。
她站在那儿,望着我,那脸上笑得跟朵花似的。阳光照在她脸上,把那眉眼照得亮亮的,把那嘴角的笑照得柔柔的。
我望着她那副得意洋洋的样子,心里那团东西又好气又好笑。
“你就知道拿我寻开心。”“没有没有,”她走过来,伸手帮我整理被我弄乱的衣领,那动作轻轻的,柔柔的,“我是认真的。你在京城这些天,就好好陪陪我。咱们去看看这京城的好地方,吃吃好吃的,玩玩好玩的——不好吗?”我望着她,望着她眼里那期待的光。
“好是好,”我说,“可我就这么待着,心里不踏实。总得做点什么。”她歪着头望着我。
“你想做什么?”我想了想。
“实在不行,我就去考大学。”她愣了一下。
“考大学?”“对。”我说,“考北大。这总可以吧?”她眨眨眼睛,然后摇了摇头。
“北大?”“怎么了?”她望着我,那眼神里有一种东西——是那种“你这人怎么什么都不知道”的无奈。
“北大有固定的报考时间,”她说,“每年一次,全国统考。下一次考核,是三个月后。”我愣住了。
“三个月?”“对。三月报名,六月考试,九月入学。现在才四月,你错过了今年的报名。”我心里那团东西往下一沉。
“那清华呢?”她摇摇头。
“一样。所有大学都是统一考试。理工大学,医科大学,农业大学,师范大学——都是同一场考试。考完了,按分数录取。”我站在那儿,心里那团东西沉得更深了。
三个月。
三个月后才能报名。
报名之后还要等考试。
考完试还要等录取。
录取之后还要念三年。
三年之后才能参加公职人员考试——这太慢了。
太慢了。
甲洛不会等我三个月。
金川部的人,不会等我三个月。
那些盯着狼部、想趁火打劫的人,不会等我三个月。
我站在那儿,心里那团东西翻来覆去地滚。
玄凝冰望着我,那眼神里有一种东西——是心疼,是那种“我知道你在想什么”的心疼。
她走过来,握住我的手。
“韩天……”我没说话。
就那么站着。
过了好一会儿,我抬起头,望着她。
“能让我去北大那边转一转吗?”她愣了一下。
“北大?”“对。”我说,“进不去,看看总行吧?我就想看看——看看那地方什么样。”她望着我,那眼神里有一种东西——是好奇,是那种“你怎么突然想去那儿”的好奇。
可她没有多问。
她想了想,然后点点头。
“行。上午我要去军务处办点事,没法陪你。不过我让马车送你去,在北大那边转转。下午我忙完了,去找你。”我点点头。
“好。”她笑了,伸手又在我脸上捏了一把。
“小白脸,乖乖等我啊。”我打开她的手。
“快去吧你。”她笑着跑了。
我站在那儿,望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院门口,然后转过身,往门口走。
门口,马车已经备好了。
还是昨晚那辆豪华的四驾马车,还是那个穿着青袍的车夫。他看见我出来,弯了弯腰。
“韩公子,将军吩咐了,送您去北京大学。”我点点头,上了车。
马车动起来,咕噜咕噜地往城东走。
马车从玄府出来,穿过那片别墅区,往城东方向走。
车夫是个四十来岁的汉子,脸黑黑的,手粗粗的,一看就是常年赶车的人。他坐在车辕上,甩着鞭子,嘴里哼着不知名的小调,那调子悠扬得很,混着马蹄声,嘚嘚的,像一首歌。
我坐在车厢里,望着窗外,心里那团东西还没完全静下来。
看了一会儿,我掀开车帘,探出头去。
“老哥,能聊几句吗?”那车夫回过头,望了我一眼,那脸上带着笑。
“韩公子,您说。”我望着他。
“你赶车多少年了?”他想了想。
“打小就跟着我爹赶车。我爹是赶车的,我也是赶车的。算起来,得有个三十年了吧。”三十年。
我点点头。
“那你见过的可不少。”他嘿嘿笑了两声。
“那是。这北京城,哪儿我没去过?哪个衙门我没送过人?那些个高楼大厦,那些个火车汽车,我都见过。”他说着,那语气里有一种东西——是骄傲,是那种“我可是见过世面的人”的骄傲。
我望着他。
“那你小时候,北京城是什么样的?”他愣了一下,然后想了想。
“小时候?那可早了。我爹说,我小时候,这北京城还不是这样的。”“什么样?”他望着前方,那眼神变得有些悠远。
“那时候,这儿还不叫北京,叫顺天府。也没什么高楼,没什么火车,没什么蒸汽车。就是普通的城,有城墙,有城门,有胡同,有院子。跟其他地方没什么两样。”他顿了顿。
“我爹说,他小时候,日子苦得很。那年头,天灾人祸,粮食不够吃,一到冬天,就有人饿死。街上常有冻死骨,瘦瘦的,硬硬的,像一截截枯木头。我爹说,他亲眼见过,一家五口,饿死了三口,剩下两口抱着哭,哭完了,还得接着活。”我听着,心里那团东西微微动了一下。
“后来呢?”“后来?”他笑了一下,“后来陛下打过来了。那时候我还小,不记事。只听我爹说,陛下进了城,也没杀人,也没放火,就是贴告示,发粮食,让那些快饿死的人活过来。然后就开始修路,盖楼,建工厂,弄火车——”他说着,那声音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东西。
“我爹说,那时候累啊。天天干活,从天亮干到天黑,累得腰都直不起来。可奇怪的是,累归累,居然没人饿死了。”他转过头,望着我,那眼睛里有一种光。
“韩公子,您说怪不怪?以前不累,可饿死人。现在累,反而不饿死了。”我望着他,没说话。
他又转过头去,望着前方。
“我爹临死前,跟我说,儿子啊,咱们大夏朝,是好的。虽然累,可累得值。你看这城市,这街道,这气派——全世界哪儿有?”他说着,那声音里带着一种自豪。
“我爹说得对。这北京城,确实好。我这些年赶车,去过多少地方?没见过比这儿更好的。那些外国人,什么西洋的,东洋的,南边的,北边的,来了都说,这地方,神了。”他嘿嘿笑着。
“神了。对,就是神了。”我听着他这些话,心里那团东西翻来覆去。
累,但不饿死。
苦,但有奔头。
这就是那个穿越者前辈,用三十多年建起来的国家。
马车继续往前走。
穿过一条又一条街道,经过一座又一座高楼。那些楼越来越高,越来越密,越来越——宏伟。
终于,马车停下来了。
车夫回过头,望着我,那脸上带着笑。
“韩公子,到了。”我掀开车帘,探出头去,往前一看——愣住了。
北大。
这就是北京大学?
我站在那儿,张着嘴,望着眼前那片建筑,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大学。
不是红墙灰瓦的老式书院。
也不是我那个世界的北大——那种灰扑扑的、挤在闹市里的老校区。
这是——这是一座城。
一座建在大学里的城。
一座巨大的、宏伟的、让人望而生畏的城。
首先映入眼帘的,是大门。
那门大得吓人。不是那种普通的校门,而是一座牌楼——可那牌楼,比我在任何地方见过的都高,都大,都气派。
牌楼是汉白玉的,白得耀眼,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牌楼顶上,是三层飞檐,一层一层往上翘,像要飞起来。飞檐上雕着龙,雕着凤,雕着麒麟,雕着各种神兽,在阳光下活灵活现的。飞檐下面,挂着一块巨大的匾,黑底金字,写着四个大字:国立北京大学。那字大得吓人,每一个都比人还高,在阳光下金光闪闪的。
牌楼底下,是门。
门是铁的,黑黑的,高高的,像两扇巨大的铁闸。门敞开着,能看见里头的光景——可那光景,让我更傻了。
牌楼后面,是一条大道。
那大道宽得吓人,比北京城的主街还宽。道上铺着青石板,一块一块,整整齐齐的,一直延伸到很远很远的地方。道两旁,种着树,那些树高大得很,枝叶繁茂,遮天蔽日的,把整条道都罩在绿荫里。
道两旁,是楼。
那些楼,不是普通的楼。
是宫殿。
真正的宫殿。
一座一座的宫殿,红墙金瓦,雕梁画栋,层层叠叠的,像把紫禁城搬了过来。可这些宫殿,比紫禁城还高,还大,还气派。有的七八层,有的十几层,有的二十几层,一层一层往上叠,叠成一座座巨大的建筑。
每一座宫殿的屋顶,都是飞檐翘角,挂着风铃,在风里叮叮当当地响。每一座宫殿的墙壁,都雕着花,描着金,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每一座宫殿的门窗,都是花窗,糊着明瓦,透出朦朦胧胧的光。
可那些宫殿之间,有烟囱。
不是工厂那种粗大的烟囱,是细细的、高高的烟囱,从宫殿的屋顶伸出来,冒着淡淡的白烟。那烟很轻,很淡,在蓝天下袅袅地飘着,像一条条白色的丝带。
宫殿之间,有管道。
那些管道也是细细的,银色的,从这座宫殿伸出来,连到那座宫殿,爬满墙壁,像一张巨大的银色的网。管道上冒着热气,滋滋地响,在阳光下蒸腾出一团团白雾。
宫殿之间,有齿轮。
那些齿轮有大有小,有的镶在墙上,有的嵌在管道中间,一个咬着一个,慢慢地转着。齿轮转动的时候,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,那声音沉沉的,闷闷的,像这座大学的呼吸。
宫殿之间,有塔。
那些塔比宫殿还高,一座一座戳向天空,塔尖尖尖的,弯弯的,像寺庙里的塔刹。可塔身上,也爬满了管道,镶满了齿轮。塔的顶上,有巨大的风扇,在风里慢慢地转着。风扇的叶片是木头的,漆着红漆,一转一转的,像巨大的风车。
风扇转动的时候,会带动塔里的什么东西,发出嗡嗡的声音。那声音从高处传下来,混着齿轮的咔嚓声,混着管道的滋滋声,混成一片巨大的、沉沉的、永不停息的声响。
可最让我震惊的,是那条大道尽头的那座建筑。
那是一座楼。
一座高得吓人的楼。
我数了数——三十层?四十层?五十层?数不清。它太高了,高得我仰起头,脖子都酸了,也看不见顶。
那楼是方的,方方正正的,像一座巨大的石碑。楼身是红色的,红得耀眼,像是用朱砂染过。楼身上雕满了花——有龙,有凤,有麒麟,有祥云,有缠枝莲,有万字不到头。那些雕花一层一层的,密密麻麻的,像要把整座楼都包起来。
楼顶上,是一座塔。
那塔也是方的,一层一层往上收,像一座宝塔。塔顶上,立着一只巨大的铜凤凰,展着翅,昂着头,像是在对着天空鸣叫。那凤凰在阳光下金光闪闪的,刺得人眼睛发疼。
塔下面,是一面巨大的钟。
那钟比我在西站见过的还大,圆圆的,亮亮的,镶在楼的正中央。钟面上刻着十二个时辰,每一个时辰都用金字标着,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钟的指针是铜的,又粗又长,慢慢地走着,一下一下的,像是在数着这座大学的时光。
钟下面,是一行大字: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。
那字也是金的,大得吓人,每一个都比人还高,在阳光下金光闪闪的。
我站在那儿,张着嘴,望着那座楼,望着那面钟,望着那行字,望着这整座——城。
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这——这是北大?
这是我那个世界的北大?
不。
这不是。
这是另一个世界的北大。
这是一个穿越者,用三十多年的时间,用他那个世界的知识,用这个世界的材料和人力,一点一点建起来的北大。
这是他的梦想。
这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遗产。
我站在那儿,望着那一切,心里那团东西翻来覆去地滚。
有震惊。
有敬畏。
还有一种说不清的——亲切。
对。
亲切。
因为我知道,建这一切的那个人,和我来自同一个地方。
因为我知道,他看见的那些东西,我也看见过。他想着的那些事,我也想过。他梦见的那些梦,我也梦见过。
我站在那儿,望着那座巨大的楼,望着那面巨大的钟,望着那行巨大的字,忽然有一种想哭的冲动。
车夫在旁边,轻轻咳了一声。
“韩公子,您没事吧?”我回过神来,转过头望着他。
他望着我,那眼神里有一种东西——是担心,是那种“您是不是被吓着了”的担心。
我摇摇头。
“没事。”他又问:“您要进去看看吗?”我望着那大门,望着那大道,望着那宫殿,望着那高塔,望着那钟楼。
然后我摇摇头。
“不了。”他愣了一下。
“不了?”我点点头。
“今天不了。”我转过身,上了马车。
车夫望着我,那眼神里满是不解。可他没多问,只是甩了甩鞭子,吆喝了一声。
马车动起来,咕噜咕噜地往回走。
我坐在车厢里,望着窗外那座巨大的、宏伟的、可怕的大学,一点一点地远去。
可我知道,我不会只来这一次。
我一定会再来的。
不是以参观者的身份。
是以学生的身份。
以北大学生的身份。
我坐在那儿,望着窗外,心里那团东西慢慢地,慢慢地,定了下来。
三个月。
三个月后,我要来考北大。
考上了,就念三年。
三年后,参加公职人员考试。
然后——然后我就能名正言顺地站在朝堂上,名正言顺地保护狼部,名正言顺地——见到那个陛下。
那个和我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人。
我深吸一口气,闭上眼睛。
马车咕噜咕噜地往前走,载着我,往玄府的方向,往那三个月后的未知,往那不知道能不能实现的梦想。
我让车夫把马车停到北大专门的停车场去,自己则在校门口站了一会儿,然后迈步走了进去。
穿过那座巨大的汉白玉牌楼,踏上那条宽阔得吓人的大道,我忽然有一种恍惚的感觉。
这味道。
空气里有股子混合的味道——煤油,机油,金属,还有一种淡淡的焦糊味,像是什么东西烧过的痕迹。这味道太熟悉了,熟悉得让我想起那个世界的工厂区,想起那些老工业城市的黄昏。
可这味道又不太一样。它不那么刺鼻,不那么呛人,反而带着一点淡淡的清香——也许是路边那些叫不出名字的花,也许是那些雕梁画栋上涂的某种特殊油漆。
学生们从我身边走过。
年轻的,男男女女,穿着各色各样的衣裳。有的穿着长衫,青的灰的,规规矩矩的;有的穿着短打,利利索索的;还有的穿着西式的洋装,领带系得紧紧的,皮鞋擦得亮亮的。他们怀里抱着书,有的厚,有的薄,有的用布包着,有的就这么夹在腋下。他们走得不慢,甚至可以说有点急,脚步匆匆的,像是有赶不完的路,做不完的事。
偶尔有人从我身边跑过去,带起一阵风,那风里有汗的味道,有书墨的味道,还有那种年轻人特有的朝气。
我站在道旁,望着那些匆匆而过的身影,忽然笑了。
挺好。
和我预想的校园,一模一样。
我继续往前走。
大道两旁,那些宫殿式的教学楼一栋一栋地掠过。有的门口挂着牌子,写着“文学院”,有的写着“理学院”,有的写着“工学院”。门口有学生进进出出,有的抱着书,有的拿着图纸,有的拎着奇奇怪怪的仪器。
再往前走,道旁开始出现一些岔路,通向更深的地方。那些岔路上也种着树,也铺着石板,也有一栋一栋的建筑。有的建筑上冒着烟,细细的,淡淡的,那是实验室里在做实验。有的建筑里传来机器的轰鸣声,闷闷的,沉沉的,那是工科学生在拆装什么东西。
我顺着一条岔路往里走。
走了没多远,忽然听见前头有人在说话。
那声音苍老,却洪亮,带着一种讲课特有的抑扬顿挫。
“……你们看,这个气缸,是整台机器的核心。蒸汽从锅炉进来,推动活塞,活塞带动连杆,连杆转动飞轮——就这么简单,又这么不简单……”我循着声音走过去。
路旁有一座凉亭。
那凉亭很大,比普通亭子大出好几倍,顶上盖着琉璃瓦,飞檐翘角,像一座小小的宫殿。可亭子四周,没有常见的栏杆和座椅,取而代之的是一圈厚厚的玻璃窗。那玻璃透透的,亮亮的,能清楚地看见里头的光景。
亭子里头,一群人围成一圈。
站在最中间的,是一个老者。
他穿着深灰色的长袍,头发花白,梳得整整齐齐的,胡子也是花白的,修剪得一丝不苟。他戴着眼镜,那眼镜片厚厚的,圆圆的,在阳光下闪着光。他手里拿着一把扳手,那扳手大大的,铁铁的,和他那斯文的样子不太相称。
他身边,是一台机器。
那机器大得很,差不多有一人多高,黑黑的,铁铁的,浑身上下都是管子、阀门、齿轮和不知道什么零件。机器顶上,有一个圆圆的烟囱,细细的,直直地戳着。机器中间,有一个大大的圆筒,那是气缸。气缸旁边,是一个大大的飞轮,铁的,圆圆的,比人还高。
机器底下,正烧着火。
那火是从一个小锅炉里烧起来的,锅炉也是铁的,圆圆的,肚子大大的。锅炉底下,有炭,红红的,旺旺的,烤得锅炉滋滋地响。锅炉上头,有一根管子,连着那机器的气缸。管子里冒着白气,热热的,滋滋地响。
整台机器,正在运转。
那飞轮慢慢地转着,一圈一圈的,咔嚓咔嚓的,带着整台机器微微颤动。那气缸一伸一缩,一伸一缩,像一头巨大的铁兽在呼吸。那烟囱里冒着白烟,袅袅的,在凉亭顶上盘旋,然后从亭子顶上的一个开口飘出去。
老教授就站在那台机器旁边,手里拿着扳手,指着那些零件,一个一个地给围在旁边的学生们讲解。
“这个阀门,是控制进气量的。开大了,进气多,机器转得快;开小了,进气少,机器转得慢。这个阀门,是控制排气的。蒸汽推动完活塞,得排出去,不然就堵住了……”学生们围成一圈,有男有女,有穿长衫的,有穿短打的,还有穿着工装裤、满手油污的。他们望着那台机器,望着那些冒着热气、转着齿轮的零件,眼睛瞪得大大的,里头满是敬畏。
那是一种对知识的敬畏。
对力量的敬畏。
对这个时代的敬畏。
老教授继续说:“这台蒸汽机,是陛下亲自设计的。三十多年前,陛下刚刚起兵的时候,就画出了图纸,让人照着做。那时候,天下大乱,哪有现在这些好材料好工具?第一台蒸汽机,做得粗糙得很,动不动就坏,三天两头要修。可就是那台粗糙的机器,给咱们带来了第一条铁路,第一列火车——”他顿了顿,那声音变得感慨起来。
“后来,咱们有了更好的材料,更好的工具,更好的工匠。这台蒸汽机,也被咱们北大学子一遍一遍地改进。如今这台,已经是第七代了。效率比第一代提高了五倍,体积缩小了一半,耗煤量减少了三分之二——”他伸手拍了拍那台机器,那动作轻轻的,像是在拍一个老朋友。
“世界最先进的蒸汽机,就是它。”学生们望着那台机器,那眼神更亮了。
有的悄悄咽了口唾沫,像是在想象自己也能造出这样的东西。
有的握紧了拳头,像是在暗暗发誓,将来要比这台更先进。
有的拿着本子,飞快地记着什么,生怕漏掉一个字。
我站在凉亭外面,隔着玻璃窗,望着里头那一切。
望着那台冒着热气、转着齿轮的机器,望着那个滔滔不绝的老教授,望着那群满眼敬畏的年轻学生——心里那团东西,忽然动了一下。
然后,那句话,不知怎么就脱口而出了。
轻轻的。
低低的。
像是自言自语。
“可惜。”那声音从我自己嘴里出来,轻得几乎听不见。
可不知怎么的,隔着那玻璃窗,里头那个老教授,忽然停下了手里的扳手,转过头来,望着我。
他望着我。
我也望着他。
隔着那玻璃窗,我们就这样望着。
然后他放下扳手,推开凉亭的门,走了出来。
那些学生们也转过头来,好奇地望着我。
老教授走到我面前,站定。
他比我矮半个头,得微微仰着脸才能看见我的眼睛。可他站在那儿,那气势,却像一座山。
他望着我,那眼镜片后面的眼睛,锐利得很。
“年轻人,你刚才说什么?”我心里微微一动。
糟了。
说漏嘴了。
可话已出口,收不回来了。
我望着他,尽量让声音平静。
“没什么,老先生。晚辈一时失言。”他盯着我,那眼神更锐利了。
“失言?你那两个字,我可听得清清楚楚——‘可惜’。”他顿了顿。
“你是在说这台蒸汽机可惜?”我张了张嘴,想解释,可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他见我不说话,那脸上的表情变得更严肃了。
“年轻人,你知道这台蒸汽机是什么吗?”我点点头。
“知道。蒸汽机。”“你知道它是谁设计的吗?”我沉默了一下。
“陛下。”他的眼睛亮了一下。
“对。陛下。”他往前走了一步,那声音沉沉的,“这台蒸汽机,是陛下亲自设计,北大工学部一代一代改进的。世界最先进,效率最高,耗煤最少的蒸汽机——就是这台。”他盯着我。
“你说它‘可惜’——你是在对陛下不敬?”那几个字,像几块石头,砸在我心上。
对陛下不敬。
这罪名,可大可小。
往小了说,是年轻人不懂事,教训两句就完了。往大了说,那是大不敬,是要掉脑袋的。
那些学生们也围了过来,站在老教授身后,望着我,那眼神里有好奇,有不忿,还有一点点——幸灾乐祸。
我站在那儿,心里那团东西翻来覆去。
说什么?
说我是穿越者?说我在另一个世界见过比这先进一百倍的内燃机?说这台让整个大夏朝引以为傲的蒸汽机,在我眼里,不过是博物馆里的老古董?
不能说。
可不说,又怎么解释那句“可惜”?
我望着老教授,望着他那锐利的眼睛,望着他身后那群等着看戏的学生。
然后我深吸一口气。
“老先生,”我说,“晚辈没有不敬的意思。陛下设计的蒸汽机,自然是极好的。北大学子一代一代改进,自然也是极用心的。这台机器,能让大夏朝有火车,有工厂,有这么多高楼大厦——晚辈只有敬佩,哪敢不敬?”他听着,那脸上的表情微微缓和了一点。
可他还是盯着我。
“那你为什么要说‘可惜’?”我望着他。
“因为——”我顿了顿,脑子飞快地转着。
“因为晚辈在想,蒸汽机虽好,可它有个绕不开的毛病。”他愣了一下。
“什么毛病?”“大。”我说,“太大,太重,太笨。火车要拖着它跑,工厂要给它盖大房子,船要给它留出大地方。它好是好,可它太占地方了。如果有一天,能有一种机器,比它小,比它轻,比它灵活,力气还不比它小——那该多好?”我说着,自己也觉得这理由有点牵强。
可这是我能想到的,最不犯忌讳的解释。
老教授听着,那眼神里的锐利,一点一点地退去。
他望着我,那眼神里,多了一点新的东西——是好奇,是那种“你这年轻人有点意思”的好奇。
“小,轻,灵活,力气还不小——”他重复着我的话,“你说的这种机器,存在吗?”我望着他。
想告诉他,存在。
在我那个世界,一百年后,蒸汽机就被内燃机取代了。更小,更轻,更灵活,力气更大。
可我张了张嘴,又闭上了。
不能说。
至少现在不能说。
我低下头。
“晚辈只是瞎想。老先生别往心里去。”他望着我。
望着我。
望着我。
然后他笑了。
那笑来得突然,像一阵风刮过,把他脸上的严肃全刮走了。他笑着,伸手拍了拍我的肩。
“年轻人,有想法是好事。瞎想也是好事。不瞎想,哪来的新东西?”我抬起头,望着他。
他望着我,那眼神里满是欣赏。
“你叫什么?哪个系的?”我愣了一下。
“我——我不是北大的学生。”他愣了一下。
“不是?”“不是。晚辈只是——只是来逛逛。”他更愣了。
“逛逛?逛北大?”他身后的学生们也愣了,互相看看,那眼神里满是不解。
老教授望着我,那眼神里有一种东西——是好奇,是那种“你这人有点意思”的好奇。
“那你刚才说的那些话——什么小啊轻啊灵活啊——是从哪儿想出来的?”我望着他。
“就是——瞎想。”他又笑了。
“瞎想能想到这个份上,不容易。”他转过身,朝那些学生们挥挥手。
“行了行了,都散了。今天的课就到这儿。回去把蒸汽机原理那一章再读一遍,明天我要提问。”学生们应了一声,又看了我一眼,然后三三两两地散了。
凉亭门口,只剩下我和老教授两个人。
他望着我,那眼神里有一种东西——是打量,是那种“让我好好看看你”的打量。
“年轻人,你既然来逛北大,那肯定不是一般人。能进这门的,都是有来头的。”我摇摇头。
“晚辈没什么来头。只是——只是暂住在京城,闲着没事,出来走走。”他望着我。
“暂住?住哪儿?”我想了想,还是实话实说。
“玄府。”他的眼睛动了一下。
“玄府?哪个玄府?”“玄家。玄凤大人的府上。”他愣住了。
那脸上的表情,变了几变。
然后他笑了,那笑里有一种东西——是恍然,是那种“原来如此”的恍然。
“玄家——你是玄家的姑爷?”我愣了一下。
“姑爷?”“可不是嘛。”他笑着,“玄家那位五姑娘,这些年多少人来求亲,一个都没看上。前些天听说她带了个年轻人回京,整个京城都传遍了。原来就是你?”我张了张嘴,想解释,可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
他摆摆手。
“行了行了,不用解释。玄家的事,老夫不掺和。不过——”他望着我,那眼神里有一种光。
“你刚才说的那些话,老夫倒是很想再听听。”我望着他。
“什么话?”“就是你说的那个——小,轻,灵活,力气还不小的机器。”他说,“你是怎么想出来的?”我站在那儿,望着这位满头白发的老教授,望着他眼里那求知的光,心里那团东西翻来覆去。
然后我开口。
“老先生,如果我说——这不是我想出来的,是我见过的——你信吗?”他愣住了。